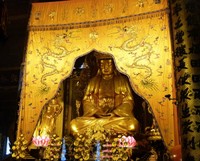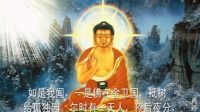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十誦律卷第十六(第三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八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有三種池水:第一池中王及夫人洗,第二池中王子大臣洗,第三池中餘人民洗。是王得道深心信佛,問諸大臣:「上人洗不?」答言:「亦洗。」王言:「上人應我池中洗。」爾時諸比丘,常初夜、中夜、後夜數數洗。一時瓶沙王欲洗,語守池人:「除人令淨,我欲往洗。」即時除卻餘人,但比丘在。知池人作是念:「王敬比丘,若遣除者王或當瞋。」便白王言:「已除諸人,但比丘在。」王言:「大善!令上人先洗。」初夜、中夜、後夜比丘洗竟便去。知池人白王言:「比丘已去。」王即往洗。王法洗遲,王洗竟時便即地了。王浴竟作是念:「我不應出城不見佛直還入城。」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卻坐一面。佛知而故問:「大王!晨朝何來?」時王以是事向佛廣說。佛爾時為王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王聞佛說法已,從坐起頭面禮足右遶而去。王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常初夜、中夜、後夜數數洗,令灌頂剎利大王自池中不得洗?」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未滿半月浴,波逸提。若滿半月浴、若過,不犯。
爾時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諸比丘不得浴故,身體垢癢煩悶吐逆。是事白佛:「願世尊,如是大熱時,聽諸比丘洗浴。」佛言:「聽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名大熱時。」
是中犯者,若比丘未至大熱時浴,波逸提。若大熱時浴,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病,以酥油塗身,不得浴故,患癢煩悶吐逆。諸比丘白佛:「願聽病因緣故浴。」佛言:「從今日聽病因緣故浴,益利病人如食無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
病者,若冷發、風發、熱發,若洗浴得差,是名病。
是中犯者,若比丘無病減半月浴,波逸提。若病,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中前著衣持缽入城乞食,時惡風起,吹衣離體塵土坌身,不得浴故煩悶吐逆。是事白佛:「願世尊聽風因緣故浴。」佛言:「從今聽風因緣故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風時。」
是中犯者,若無風因緣浴,波逸提。若有風因緣浴,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著新染衣入城乞食,值雨衣濕染汗著身生疥疱,不得浴故癢悶吐逆。諸比丘白佛:「願世尊聽雨因緣故浴。」佛言:「聽雨因緣故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風時、雨時。」
是中犯者,若無雨因緣浴,波逸提。有雨因緣浴,不犯。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諸比丘作新佛圖,擔土持泥墼塼草等,麁泥細泥黑白泥治,不得浴故,癢悶吐逆疲極不除。是事白佛:「願世尊聽作因緣故浴。」佛言:「聽作因緣故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風時、雨時、作時。」
作者,乃至掃五掃箒僧坊地,亦名為作。
是中犯者,若比丘無作因緣浴,波逸提。若作因緣者,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從憍薩羅遊行向舍衛國,是土地多土塵,行時塵士坌身,不得浴故,身體癢悶吐逆。是事白佛:「願世尊聽行因緣故浴。」佛言:「聽行因緣故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風時、雨時、作時、行時。」
行者,乃至半由旬若來若去。
是中犯者,若比丘昨日來今日浴,波逸提。明日欲去今日浴,波逸提。若至半由旬來去浴者,不犯。若比丘無是六因緣,減半月浴,波逸提。若有因緣,不語餘比丘輒浴者,突吉羅。(六十竟)
佛在維耶離國。爾時維耶離國諸王子,出園林中學射,門扇孔仰射空中,筈筈相拄。爾時迦留陀夷,中前著衣持缽入城乞食,遙見諸王子作如是射,見已便笑。諸王子言:「何以故笑?我等射不好耶?」答言:「不好。」問言:「汝能不?」答言:「能。」「若能便射。」迦留陀夷言:「我等法不應捉弓箭。」諸王子言:「此有木弓可用。」即與木弓。張時有飛鳥空中迴旋,迦留陀夷放箭,圍繞不令得出。諸王子言:「何故不著?」答言:「射著何足為難?」諸王子言:「不爾。若能著者,便應令著,莫但虛語。」即憍慢言:「汝等欲令射著何處?」王子言:「欲令著右眼。」即著右眼,是鳥即死。爾時諸王子皆慚愧妬瞋恨言:「沙門釋子能故奪畜生命。」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故奪畜生命?」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故奪畜生命?」種種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逸提。」
奪命者,若自奪、若教他奪。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三種奪畜生命,得波逸提:自、教、遣使。自者,若比丘自作自奪畜生命。教者,語他言:「是畜生捉縛打殺。」若他受教殺者,是比丘得波逸提。遣使者,若比丘語人言:「汝識某畜生不?」答言:「識。」「汝往捉縛打殺。」使往捉縛打殺者,比丘得波逸提。
又比丘有三種奪畜生命,得波逸提:一者用受色,二者用不受色,三者用受不受色。受色者,若比丘以手打畜生,若足、若頭、若餘身份,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不受色者,若比丘以木瓦、石刀、矟弓箭、若木段、白鑞段、鉛錫段遙擲畜生,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受不受色者,若以手捉木瓦石刀矟弓箭木段白鑞段鉛錫段就打,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
若比丘不以受色、不受色、受不受色,為殺故,以毒藥著畜生眼中、耳中、鼻中、口中、身上瘡中,著飲食中、臥處、行處,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
若比丘不以受色、不受色、受不受色,不以毒藥,為殺故,作憂多殺、頭多殺,作弶網撥毘陀羅殺、似毘陀羅殺、斷命殺、墮胎殺、按腹殺、推著水火中殺、推著坑中殺,遣令道中死,乃至母胎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於中起方便,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六十一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共十七群比丘鬪諍相罵心不和合。時六群比丘共十七群比丘鬪諍相罵已,六群比丘欲令十七群比丘疑悔故,作是言:「汝等不滿二十歲受具足戒,若人不滿二十歲受具足戒者,不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是人得是語已,愁憂疑悔啼泣。諸比丘問:「何故啼耶?」答言:「六群比丘令我疑悔云:『我等不滿二十受具足戒,若不滿二十受具足戒者,不名得具戒。若不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我等聞是語,疑悔故啼。」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故令他疑悔?」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故令他比丘疑悔?」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令餘比丘疑悔,使須臾時心不安隱,以是因緣無異,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六事:一者生,二者受具戒,三者犯,四者問,五者物,六者法。
生者,若比丘問餘比丘:「汝何時生?」答言:「某王時生,某大臣時生、某豐樂時、某饑儉時、某安隱時、某疾病時生。」即復言:「若人某王時生、某大臣時、若豐樂、饑儉、安隱、疫病時生者,是人不滿二十歲。若人不滿二十,不得受具足戒。若不得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他比丘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又比丘問他比丘言:「汝掖下何時生毛?口邊何時生須?咽喉何時現?」若言:「某王時、某大臣時、若豐樂、饑儉、安隱、疫病時生。」即復言:「若人某王時、某大臣時、若豐樂、饑儉、安隱、疫病時,生毛、生須、咽喉現者,是人不滿二十。若人不滿二十受具足戒,不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生。
受具足戒者,若比丘問他比丘言:「汝何時受具足戒?」答言:「某王時、某大臣時、若豐樂、饑儉、安隱、疫病時受具足戒。」即復言:「若人某王時、某大臣時、若豐樂、饑儉、安隱、疫病時受具足戒者,是人不得具足戒。不得具足戒者,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又比丘問他比丘:「誰是汝具足戒和上?誰作阿闍梨?誰作教師?」答言:「某作和上、某作阿闍梨、某作教師。」即復言:「若某作和上、某作阿闍梨、某作教師,是人不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又比丘問他比丘言:「汝於十眾中受具足戒,於五眾中受具戒耶?」答言:「十眾中。」即復言:「若如是十眾中受具戒,是人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戒者,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又比丘問他比丘:「汝於界內受具戒、界外受?」答言:「界內受。」即復言:「若界內受,是人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足戒者,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受具足戒。
犯者,若比丘語他比丘言:「汝犯僧伽婆尸沙罪、犯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者,是人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犯。
問者,若比丘問他比丘:「汝入某聚落、行某巷、至某家、坐某處、共某女人語、到某比丘尼坊、共某比丘尼語耶?」答言:「我入某聚落、行某巷、到某家、坐某處、共某女人語、到某比丘尼坊、共某比丘尼語。」即復言:「若比丘入某聚落、行某巷、到某家、坐某處、共某女人語、到某比丘尼坊、共某比丘尼語者,是人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問。
物者,若比丘語餘比丘:「汝誰同心用缽?誰同心用衣,用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答言:「與某同心用缽、衣、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即復言:「若比丘與某同心用衣、缽、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者,是人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物。
法者,若比丘語他比丘:「莫多畜衣、莫數數食、莫別眾食、莫他不請入其舍、莫非時入聚落、莫不著僧伽梨入村邑。」若比丘答言:「我受迦絺那衣。」即復言:「若比丘隨意多畜衣、數數食、別眾食、他不請入其舍、非時入聚落、不著僧伽梨入村邑者,是人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法。
若比丘以是六事,令他比丘疑悔,皆波逸提。除是六事,以餘事令他比丘疑悔,突吉羅。若除比丘以是六事,以餘因緣令餘人疑悔,皆突吉羅。(六十二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十七群比丘中,有一白衣小兒憙笑。時十七群比丘以憙笑故,用指擊攊,小兒多笑乃至氣絕,不能動手足便死。時十七群比丘生疑:「我等將無得波羅夷?」是事白佛。佛知故問十七群比丘:「汝以何心作?」答言:「我以戲笑故。」佛言:「若爾者不犯殺。」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指擊攊他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一指擊攊他,一波逸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指,十波逸提。若以木石擊攊他,突吉羅。(六十三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波斯匿王有洗浴池,處處作堰。時十七群比丘共相謂言:「至阿脂羅河上洗浴去來。」十七群比丘中,有一比丘得禪定故,實不樂往,為護餘人意故去。諸比丘皆到阿脂羅河岸上,脫衣入河中作種種戲,或手拍水、或倒沒、或如魚轉、或掉臂、或兩手把水、或一手、或仰浮。是洗浴處,王殿上悉得遙見。時王與末利夫人於殿上受五欲樂,女妓自娛。時王遙見十七群比丘在水中種種戲,語末利夫人:「此是汝所尊重者,於水中作如是種種麁戲。」夫人答言:「王何以言?看此是年少耳!王何不言:『看摩訶迦葉、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爾時是中得禪定者不洗,在別處坐禪,聞是二語:王語、夫人語。聞已語餘比丘言:「汝洗己足勿復更洗,當上岸著衣,皆盛滿澡罐水著前,結加趺坐。」如是教已,即皆上岸著衣盛滿瓶水著前,結加趺坐。時得定者,以神通力令瓶水各各在前空中去,令諸比丘大坐閉眼隨後而去。時末利夫人見已語王言:「此是我所尊重者也,作如是行,乃至王所不見處。」時夫人即遣使詣佛所,白佛言:「是王常憙出比丘過罪,以此水中洗戲故,願令諸比丘莫復此中洗。」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十七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十七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水中作種種戲,以手拍水倒沒、或如魚轉、或兩手把水、或一手、或仰浮?」種種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水中戲,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八種:一者作喜,二者作樂,三者作笑,四者作戲,五者弄水,六者令他喜,七者令他樂,八者令他笑。若比丘欲作喜故,以手拍水,波逸提。若於水中倒沒、或轉如魚、或一臂兩臂浮、或身踴、或仰浮,皆波逸提。若比丘欲作樂、作笑、作戲弄水,令他喜、令他樂、令他笑故,作是種種浮戲,皆波逸提。乃至盤上有水、若坐床上有水,以指畫之,突吉羅。
不犯者,若學浮、若直渡,不犯。(六十四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阿那律,從憍薩羅遊行向舍衛國,到一聚落無僧坊處欲宿。是阿那律本國王子,性貴故不憙問小小事,又不知何人可問、不可問。見聚落中諸立年少,即往問言:「是聚落中誰能與出家人宿處?」時聚落中有一淫女,是諸年少欲戲弄比丘故,答言:「某處可宿。」即往到女門前立彈指。時女人出看,見阿那律端正有威德顏色可愛,見已淫欲心發。女人問言:「汝何所索?」答言:「寄宿。」女言:「可得。」即入與坐處,共相問訊,然後乃坐。女勅家人,辦種種飲食、種種莊嚴供養是客。即敷大床好褥被枕,即此床邊更著一床,自為身故。是女人初夜請比丘作不淨事:「我當為汝供給捺腳。」比丘答言:「我是斷淫欲人,莫說是事。」女人意念:「此必有欲,但以初至疲極故。」至中夜更語,猶故不從。至後夜復語,亦故不從。至地了時女語比丘言:「國王、大臣有持百金錢來,我不肯從。二百、三百、四百、五百我亦不從。我於今夜三自相請,而汝不肯。汝於比丘所應得法,必當得之。若不欲爾者,為愍我故受我施食。」阿那律念言:「我道中行必,當復須食。」作是念已即默然受。知默然受已,即時辦飲食,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飽滿已,知洗手攝缽竟,取小床在前坐聽說法。時阿那律觀女人心本末因緣,為說次第法,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女人見法聞法知法入法,度疑悔不隨他,於佛法中得自在心無所畏。從坐處起,頭面禮阿那律足言:「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盡形作佛優婆夷。」時阿那律更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從是已來此家常供給沙門釋子衣服飲食。是淫女少多送阿那律已便還。爾時阿那律漸到舍衛國,脫衣缽著一處,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忍不?足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佛即以如是語勞問阿那律:「忍不?足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阿那律答言:「世尊!忍足、乞食不難、道路不疲。」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阿那律雖離欲得阿羅漢,不應與女人共宿。如熟飲食人之所欲,女人於男亦復如是。」種種因緣訶責不應與女人共宿:「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同捨宿,波逸提。」
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是。人女若臥若坐名為宿。象若倚若立亦名宿。駝馬、牛羊若臥若立亦名宿。鵝鴈、孔雀、雞,若一腳立、若持頭置項上亦名宿。
捨者有四種:一切覆一切障、一切障不覆、一切覆不障、一切覆少障。
是中犯者,若比丘是四種捨中共女人宿,皆波逸提。若起還臥,更得波逸提。隨起還臥,一一波逸提。不犯者,通夜坐不臥。乃至他捨有女人宿,孔容貓子入處,是中宿波逸提。(六十五竟)
佛在維耶離國摩俱羅山中,爾時與侍者象守比丘俱。諸佛侍者法,佛未入房不得先入。時佛初夜露地經行,爾時小雨墮,釋提桓因作是念:「佛今在露地經行小雨墮,我何不變作琉璃窟,令佛在中經行。」即變化作,佛在中經行,帝釋隨後。佛經行久,是象守比丘風雨所惱,作是念:「當以何方便令佛入舍,我當得入?」爾時摩俱羅山中所有人民,小兒啼時則以婆俱羅夜叉怖之令止。時象守反被俱執,在經行道頭立,以兩手覆兩耳語佛言:「婆俱羅夜叉來。」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云何佛法中乃有是癡人?」佛言:「憍尸迦!我家廣大,此人現身亦當得漏盡,所作已辦更不復受後有。」佛種種因緣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釋提桓因聞佛示教利喜已,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釋去不久,佛入自房敷坐床坐。是夜過已,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象守比丘言:「癡人!云何能恐怖如來佛世尊?汝癡人!佛者無怖畏、衣毛不竪。」爾時佛說偈言:
「佛於自法中, 通達無礙智;
有人可以此, 婆俱夜叉恐。
佛於自法中, 通達無礙智;
是故能過度, 生老病死苦。
佛於自法中, 通達無礙智;
是故能除滅, 諸結使煩惱。」
佛種種因緣訶責象守比丘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恐怖他比丘、若教他恐怖,乃至戲笑,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六種:色、聲、香、味、觸、法。色者,若比丘作象色、若作馬色、羝羊色、水牛色,作如是等可畏色恐怖比丘,若能令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色。聲者,若比丘作象聲、馬聲、車聲、步聲、羝羊聲、水牛聲,作如是等可畏聲恐怖他比丘,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聲。香者,若比丘作好香、若作臭、若等分香、若作希有香,作如是等香恐怖他比丘,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香。味者,若比丘問他比丘:「汝今日用何物噉飯?」答言:「用酪酥。」又言:「若用酪酥噉飯者,是人得癩癬病。」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若比丘復問他比丘:「汝今日以何物噉飯?」答言:「用酪酥毘羅漿。」又言:「若人用酪酥毘羅漿噉飯者,是人得癩癬病。」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又比丘問餘比丘:「汝今日以何物噉飯?」答言:「以酥豬肉。」又言:「若人用酥豬肉噉飯者,是人得癩癬病。」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味。觸者,若比丘持身令堅,若麁、若軟、若細滑、若澁,令身皆異,以觸他比丘,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觸。法者,若比丘語餘比丘:「汝莫於生草中大小便,當墮地獄餓鬼畜生。」是比丘答言:「我自知是法。」又言:「若比丘生草中大小便者,是比丘便墮地獄餓鬼畜生。」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法。若比丘以是六事恐怖比丘,波逸提。除是六事,以餘事恐怖比丘,突吉羅。若以六事及餘事恐怖餘人,突吉羅。(六十六竟)
佛在舍衛國。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是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還家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敷坐處。爾時諸比丘,早起持衣缽著露地待時到。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共鬪諍不相憙。時六群比丘,取十七群比丘衣缽藏著異處。時十七群比丘來求衣缽,久覓不得。十七群比丘法,有所作事皆共相語。時失衣者語餘者言:「我不知衣缽處,相助求覓。」於是中間,居士敷坐處已,遣使白佛:「時到,飲食已辦,佛自知時。」諸比丘僧往居士捨,佛自房住迎食分。居士見僧坐已,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自恣飽滿已,知僧攝缽自行水竟,取小床在僧前坐,欲聽說法。上座說法已,及餘比丘各從坐起,出居士捨。十七群比丘爾許時覓衣始得來入,眾僧出時見已問言:「何故在後?」答言:「六群比丘藏我衣缽,久覓始得。」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藏他比丘衣缽,求覓時間垂當斷食?」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藏他比丘衣缽,求覓時間垂當斷食?」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藏他比丘缽、若衣、戶鉤、革屣、針筒,如是隨法所須物,若自藏、若教他藏,乃至戲笑,波逸提。」
自藏者,自手藏。教藏者,教他藏。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藏他比丘缽,彼比丘若覓不得,是比丘得波逸提;若覓得,突吉羅。若衣、戶鉤、革屣、針筒,若覓不得,波逸提;若覓得,突吉羅。若藏空針筒,彼比丘若覓不得,突吉羅;若得,亦突吉羅。(六十七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性嬾惰,不憙自浣染衣割截篸縫,若有衣可浣染割截篸縫者,便持是衣與比丘、若比丘尼、式叉摩尼、若沙彌、沙彌尼。諸人生自衣想,浣染割截篸縫作衣竟。爾時六群比丘知衣已成,便往索言:「此衣何以久不還我?」軟語不得,即強奪取。爾時諸比丘,不見六群比丘浣染割截篸縫衣時,但見著新衣。諸比丘問六群比丘言:「不見汝浣染割截篸縫衣時,但見著新衣。」六群比丘言:「我等有可浣染割截篸縫衣,持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諸人是衣中生自衣想,浣染作衣竟,我便往索:『此衣何以久不還我?』軟語不得,即強奪取著。以是因緣故,汝等不見我浣染割截篸縫衣時,但見我著新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他不還便強奪取著?」諸比丘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他不還便強奪取著?」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他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他不還,便強奪取著,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他不還,便奪取著,波逸提。
爾時諸比丘不知長衣當云何畜?是事白佛,佛言:「應作淨畜。」有比丘現前作淨,與他衣已,他不肯還,即生鬪諍。是事白佛,佛言:「不應現前與。」爾時有比丘與二、三人衣,作是言:「我所有衣缽皆與某甲。」某甲二、三人,如是散亂不應淨法。是事白佛,佛言:「不應與二、三人,應好思惟籌量與一好人。應作是言:『我衣缽皆與某甲一人。』從今日比丘有應常用衣,不應與他,若遣與、若作淨、若受持。」比丘有衣應與他者,與六群比丘中一人,是人受衣已便不肯還,餘比丘亦得懊惱,不能得好同心比丘故。又一時夏末月,佛遊行諸國,餘比丘皆著新染衣。是一比丘著故弊衣,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汝何故著弊故衣?」比丘答言:「世尊!我有衣應淨故,與六群比丘中一人,受我衣缽已便不肯還。餘比丘亦得懊惱,不得好同心比丘故。」佛言:「是施不名真實,為清淨因緣故與,即時是比丘應還索取,若得者好,若不得者應強奪取,應教彼作突吉羅罪悔過。從今日比丘所有常用衣,隨意不應與他;若作淨、若受持、若施人,不犯。」(六十八竟)
佛在維耶離國。爾時有彌多羅浮摩比丘,作是念:「我以無根波羅夷法,謗陀驃比丘力士子不能得成,是事無根故。又以小因緣作波羅夷謗,亦不得成,無小因緣故。我今當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陀驃比丘力士子。」作是念已,即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陀驃比丘。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種種因緣,訶責彌多羅浮摩比丘:「云何名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清淨梵行比丘?」諸比丘種種因緣,訶責彌多羅浮摩比丘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清淨梵行比丘?」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他比丘,波逸提。」
無根者,根有三種:若見、若聞、若疑。
僧伽婆尸沙者,十三僧伽婆尸沙中隨彼所說。
謗者,他所不作,強言作罪。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不清淨比丘,十一種犯、五種不犯。十一種犯者,若不見、不聞、不疑、若見忘、若聞忘、若疑忘,若聞信聞、若聞不信聞,聞已言我疑,疑已言我見,疑已言我聞,是名十一種犯。五種不犯者,是事若見、若聞、若疑,見已不忘、聞已不忘,是名五種不犯。不清淨比丘、似清淨比丘亦如是。
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清淨比丘,十種犯、四種不犯。十種犯者,不見、不聞、不疑、若聞忘、疑忘、若聞信聞、若聞不信聞、聞已言疑、疑已言見、疑已言聞,是名十種犯。四種不犯者,若聞、若疑、若聞不忘、若疑不忘。清淨比丘、似不清淨亦如是。(六十九竟)
佛在維耶離。去維耶離城不遠,有織師聚落,是中一織師婦,有小事不隨夫言,夫以手腳痛打驅出捨。是女父母家,在維耶離城中。婦作是念:「我當還歸。」作是念時,有迦留羅提舍比丘,從跋耆國遊行向維耶離。是婦出外見是比丘,問言:「善人!那去?」答言:「向維耶離。」婦言:「俱去。」即便俱發。爾時以染心相看調戲、大語掉手臂行,作種種不淨事。時織師還作是念:「我婦或當走去。」即出捨求婦,不得。諸織師法,有事皆相佐助,即語餘織師言:「我婦走去。」諸織師即於要道中覓。是夫作是念:「是婦生在維耶離,必當還歸。」即自向維耶離道中,見婦與向比丘俱行。即往捉比丘以衣系項言:「汝比丘法應將我婦去耶?」答言:「我不將去,我自向維耶離,汝婦自隨我來。」夫言:「云何肯直首?」即以手腳打比丘。婦見打比丘故,語夫言:「何以打他?此比丘不將我來,我自向維耶離。」夫語婦言:「小婢!汝必共作不淨事。」復更以手腳打比丘已放去。是迦留羅提舍比丘,起如是惡事便去,到維耶離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如是罪及餘過罪,皆由與女人共期道行故。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共期道行,乃至一聚落,波逸提。」
女人者,有命女人堪作淫欲。
期者,有二種:若比丘作期、若女人作期。
道者,有二種:水道、陸道。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女人共期陸道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若無聚落空地行,乃至一拘盧舍,波逸提;中道還,突吉羅。水道亦如是。
不犯者,若比丘不共期行,若與國王、夫人共道行,不犯。(七十竟)
佛在維耶離。爾時諸比丘,從跋耆國遊行向維耶離,是道多草木。諸比丘失道,入薩羅樹林中。爾時有賊,作惡事竟先在林中。諸賊見比丘作是言:「比丘那去?」答言:「向維耶離。」賊言:「此非維耶離道。」諸比丘言:「我等亦知非向維耶離道,我等失道故。」諸比丘問賊:「汝等那去?」答言:「向維耶離。」諸比丘言:「我曹與汝等共去。」諸賊言:「不知我等是賊耶?我等或隨道行、或不隨道行、或從濟渡恆河、或不從濟渡、或由門入、或不由門入,若共我等去者,或得衰惱事。」諸比丘言:「我等以失道,有事無事為當共去。」答言:「隨意。」即與賊俱去,不由濟渡恆河時,為邏人所捉。邏人問諸比丘:「汝等亦是賊耶?」答言:「我等非賊,以失道故。」邏人即看無異財物,邏人言:「汝肯直首耶?當將詣官治。」眾官問言:「汝等亦是賊耶?」答言:「我等非賊,以失道故。」眾官即看無異財物。時斷事人信佛法故,作是言:「沙門釋子不作是惡事,必是失道。」語比丘言:「今放汝去,後莫復與惡人共道行。」諸比丘起如是大惡事已便去,以是事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如是罪及過是罪,以與賊眾共道行故。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賊共期同道行,乃至一聚落,波逸提。」
賊者,偷象馬牛羊,到小聚落抄奪他物。
期者,有二種:若比丘作期、若賊作期。
道者,有二種:水道、陸道。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陸道與賊共期,從一聚落至一聚落,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若無聚落空地,乃至一拘盧舍,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水道行亦如是。
不犯者,若不期不犯。若險難處賊送度者,不犯。(七十一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王舍城中,十七群年少富貴家子、柔軟樂人和提等,未滿二十歲,長老目揵連與受具戒。是人晡時饑急故,於僧坊內發大音聲,作小兒啼。佛聞僧坊內小兒啼聲,知而故問阿難:「何故僧坊內有小兒啼聲?」阿難答言:「世尊!是王舍城中,有十七群年少富貴家子、柔軟樂人未滿二十歲,長老目揵連與受具戒。晡時饑急,是故僧坊內發大音聲作小兒啼。」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大目揵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目揵連:「汝不知時、不知量,趣得便與受具足戒。汝云何不滿二十歲人與受具戒?何以故?不滿二十歲人,不能堪忍寒熱、飢渴、蚊虻、風雨、蛇毒所螫、他人惡口、苦急奪命、重病,皆不能堪忍,是不滿二十歲人未成就故。」佛言:「滿二十歲人,能堪忍寒熱、飢渴、蚊虻、風雨、蛇毒所螫、他人惡口、苦急奪命、重病,皆能堪忍,以成就故。」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未滿二十歲人與受具足戒,波逸提。是人不得具足戒,諸比丘亦可訶。是事應爾。」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人不滿二十歲、自想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者亦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自想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犯,諸比丘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自想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不滿二十歲,忘、不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亦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忘、不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忘、不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不滿二十歲,不自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者亦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不自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不自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不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者亦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者無罪,諸比丘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我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者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滿二十歲,自想滿二十,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諸比丘無罪,共事共住者亦無罪。
又人滿二十歲,自想滿二十,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者亦得罪。
又人滿二十,自想滿二十,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滿二十歲,忘、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得戒,諸比丘無罪,共事共住亦無罪。
又人滿二十,忘、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不得戒,共事共住得罪,諸比丘亦得罪。
又人滿二十,忘、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滿二十歲,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得戒,諸比丘無罪,共事共住亦無罪。
又人滿二十歲,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不得戒,共事共住得罪,諸比丘亦得罪。
又人滿二十歲,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得戒,諸比丘無罪,共事共住亦無罪。
又人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亦得罪。
又人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我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七十二竟)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阿羅毘比丘,自手掘地作牆基、掘渠池井、掘泥處。有居士是外道弟子,說地中有命根,是人以嫉心故,訶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功德。』而奪一根眾生命。」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阿羅毘比丘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自手掘地,掘作牆基、掘渠池井、掘泥處?」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手掘地、若教他掘,作是言:『汝掘是處。』波逸提。」
地者,有二種:生地、不生地、頹牆土、石底蟻封、土聚。生地者,若多雨國土八月地生,若少雨國土四月地生,是名生地。除是名不生地。
自掘者,手自掘。
教他掘者,教他人掘。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掘不生地,隨一一掘,突吉羅。若頹牆土、石底蟻封、土聚,若掘者,隨一一掘,突吉羅。若比丘掘生地,隨一一掘,波逸提。若掘作牆基、若掘渠池井,隨一一掘,波逸提。若掘泥處,乃至沒膝處掘取,隨一一掘,突吉羅。若手畫地,乃至沒芥子,一一畫,突吉羅。
若比丘作師匠,欲新起佛圖僧坊,畫地作模像處所,不犯。餘比丘畵者,犯罪。若生金銀、硨璩、瑪瑙、硃砂鑛處,若掘是處,不犯。若生鐵鑛處,銅、白鑞、鉛錫鑛處;若雌黃、赭土、白墡處;若生石處、生黑石處、沙處鹽地,掘者不犯。(七十三竟)
十誦律卷第十六
上篇:十誦律
下篇: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