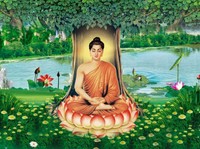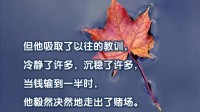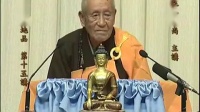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
我們看第七科,明藏性即識大性。這個藏性就是我們現前一念心性。這個「識」,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識的了別性。就是,這個六識其實是我們一念心性當下具足的,六識的作用是假借事相的因緣而顯現的,所謂的相妄性真。
分四科:一,破妄執;二,明大均;三,顯理性;四,斥迷惑。
先看「總標識性」。
阿難!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出。汝今遍觀此會聖眾,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那,此目犍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
首先,我們把這個根跟識的關係說一下。六根是五俱意識的第一剎那,它是一種自性的分別,不帶名言的,所以它得到的是諸法的相狀。六識是五俱意識第二念以後,我們第六意識產生一種名言分別,產生很多的思想。你看到這個花,這個花很漂亮,開始就著這個花產生很多很多的名言妄想,這個就是所謂的計度分別。一個是帶名言,一個不帶名言。
好,那麼我們看這個六識。首先我們看六識的體性。說「阿難!識性無源。」眼耳鼻舌身意這六種識,它的體性是沒有一個根源的,來無所從,去無所止。其實,沒有根源,簡單地講就是它遍滿的意思,它是週遍法界,沒有固定的處所。它必須假借六種的根跟六種的塵,就是六根去攀緣六塵,相互作用,這個中間才創造六識的了別出來。它的作用是這樣子。
根塵的相互作用創造六識的關係,這以下就詳細說明。比方說,「汝今遍觀此會聖眾」,說你在這個楞嚴法會當中,你用你的眼睛去普遍觀察諸位參加法會的聖眾。「遍觀」,正是講的是能見的根;「此會聖眾」是所見之塵。那麼根塵的作用,就產生了一定的效果。我們剛開始,「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我們剛開始依止眼根,就循著次第一一地觀察,在我們眼睛的範圍當中觀察,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聖眾。這些聖眾就好像鏡子當中顯現一種影像,而我們能夠對這個影像有所了知,但是不能產生一種名言的分別。
不能產生名言分別,不能帶動名言,不能帶動種種的思想,只有了知它的形相。然後慢慢地,「汝識於中,次第標指。」等到根塵的作用第二剎那以後,就帶動了所謂六識的產生。那麼六識就能夠對於這個所觀境一一明白地指出:喔,這是文殊菩薩,這是富樓那尊者,這是目犍連尊者,這是須菩提尊者,這是舍利弗尊者。我們就能夠把這些影像加上很多很多的名稱,對這個名稱去思惟它的功德:目犍連尊者神通第一,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等等。這種思惟的功能就是六識;只是取它的相狀,這是六根。這個地方把根跟識分清楚。
我們看下一段,征問原由。
此識了知,為生於見?為生於相?為生虛空?為無所因突然而出?
現在正式進入主題了。說這個眼識產生了別的功能,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呢?是從眼根的見產生的?還是生於外在的塵相?還是生於虛空?還是沒有因緣、突然而有呢?我們先作一個假設,說這六識是有自體的,有自體就有地方來,看它從什麼地方來。
我們再看「別破妄執」。先破因根生。
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暗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汝見,見性尚無,從何發識?
說,阿難!假設我們眼識的了別性是從眼根而生,那這等於是自生,眼根創造了眼識。但事實上,如果沒有明暗色空這四種塵境的刺激,在沒有四種外塵的情況之下,我們能見的根都不能生起作用。能見的根尚且不能生起明瞭,又怎麼能夠發動這個了別的識呢?沒有外境,連根都不能生起,不要說識。所以說自生不合理。
下面破因塵生。
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暗,明暗不矚,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從何發?
假設我們這個眼識的了別,是從外相、四種的塵相所生,不是從見根而生。那麼如此一來,在缺乏能見的眼根的情況之下,我們既看不到明相,也看不到暗相。明相暗相都不可見,乃至於一切的色法之相、一切的虛空之相都見不到。那麼種種的塵相尚且見不到,眼識又怎麼發動呢?眼識的目的就是了別這些塵相,結果你連塵相都看不到,那要怎麼了別呢?所以不能夠說從塵生。
我們看,破從空生。
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辨,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則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
說這個眼識是有自體的,是生於虛空,從虛空而來,那麼這種情況叫作「非相非見」。既然它從虛空而來,那麼它不須假借外在的塵相,又不必假借內在的眼根,這叫「非相非見」。那麼在「非見」的情況下,沒有能見的眼根,我們事實上是不能辨別明暗色空之相。那麼在「非相」的情況之下,沒有所見的明暗色空之相,這個「非相滅緣」,如果沒有所見的明暗色空之相,那麼它的因緣也就消失了,見聞覺知也就不能安立了。沒有所見的塵相,那所緣的塵相消失了以後,其實能見的眼根也沒辦法存在了。
所以,「處此二非」,在此「非相非見」的二非當中,「空則同無,有非同物。」那麼這種情況,你說虛空能夠生起眼識,在非見非相的沒有見也沒有相的情況之下,虛空就好像是跟「無」一樣,又怎麼能夠發動識呢?「有非同物」,好,即使你說虛空是存在的,但是虛空又不像萬物一樣有種種的形相,它是無形無相,那麼它創造那個識,縱然能夠發動識,「欲何分別?」又能夠分別什麼呢?因為虛空是處在一種非見非相的情況之下,就算它發動識又有什麼作用呢?這個識就是在了別塵相的啊,結果它的塵相消失了,你發動這個識又有什麼作用呢?所以這個空產生識不合理。
我們看,破無因生。
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
說是眼識是沒有因緣,那怎麼有呢?是突然之間冒出來的,沒有任何理由。那佛陀就反問了,為什麼你的眼識不在面對太陽的時候,突然間看見晚上的月亮而生起了別呢?因為你說無因緣嘛,你為什麼不面對太陽卻看到月亮呢?不可能嘛。你面對太陽,你只看到太陽;你面對月亮,你只看到月亮。你因為太陽的因緣而看到太陽,因為月亮的因緣而看到月亮,這個都是要因緣,不是說沒有因緣就可以出現的。你要拜佛,你要有一個佛像。就是說,什麼東西都要有因緣的,所以無因緣生是不合理的。
淨界法師《楞嚴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