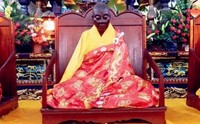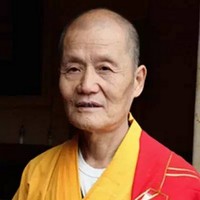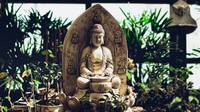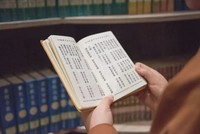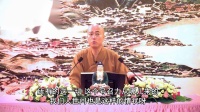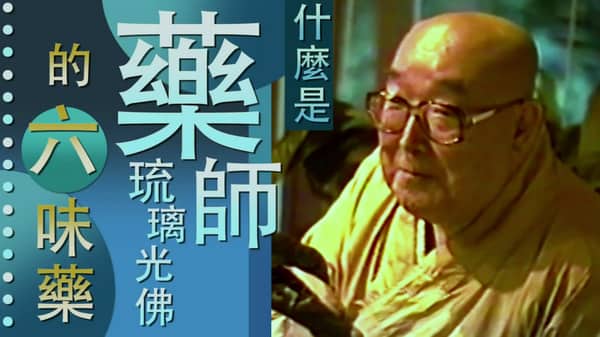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
其定心亦有寬急之相。定心急病相者,由坐中攝心用念,因此入定,是故上向胸臆急痛。當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患自差矣!
這個地方講寬急相,先講急。這個急,就是你用功太過急切。
在坐中攝心用念,這個是正確的方法。我們要能夠攝心,主要就是念,用念攝心,用你的念力,不能念要它念,不能專要它專,用明記不忘的念力來攝持這一念攀緣心,這個時候是很正常。但是他下面出了毛病:是故上向胸臆急痛,就是上面的胸口痛。
有些人他念佛越念會越快,剛開始坐的時候,速度很正常,調和他的氣息,但是他坐一段時間以後越念越快,這個人多數個性比較急躁。或者他個性不急躁,但是他求好心切,要趕快有所成就,這個時候用功過猛,胸口就痛。
那怎麼辦呢?當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患自差矣!這種急躁的人,你看打佛七的時候,他一開始坐得很正常,念個十分鐘以後,他肩膀就聳起來了。這肩膀一聳起來,表示他開始緊張了,他的心開始急躁了,他心中越念越快,這種情況就容易胸痛,再嚴重的話就頭痛。這個時候,當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患自差矣。
如果是修行引生的病痛,如果有這種情況,比如說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同參道友因為修行產生了病痛,只要你暫時不修行幾天,它就好了。因為本來佛法的專注它是要你在放鬆的狀態、寂靜的狀態專注,但是有些人他一專注,肌肉就繃緊,就緊張,肌肉一繃緊就容易有問題。所以你這個時候讓他放鬆,你放鬆個幾天不修行了,它就好了,它自然就過去了。
若心寬病相者,覺心志散慢,身好逶迤,或口中涎流,或時暗晦,爾時應當斂身急念,令心住緣中,身體相持,以此為治。
這個是寬,就是這個身體太寬了,心志散慢,身好逶迤。這個急病相,大部分都是初學容易發生;這個老參,老修行,他就容易有寬相。修行久了,他也提不起勁了,心志散慢,身好逶迤,內心對於這個佛號,你說,他有沒有念佛?他可還是在念佛,嘴巴也在念佛,但是嘴巴念佛,他也沒打妄想。你說他打妄想,他心中也沒有其它妄想,但是心志散漫,他就是那個能念的心,那個念力薄弱,他對佛號那個明記不忘的念力,沒有那個念力,很薄弱,他心中有佛號也沒有妄想,但是念力也薄弱,就是這樣,心志散漫,執持佛號那個執持的力量非常薄弱。
身體萎靡不振,身體坐得也不正直了,看起來坐在那個地方沒什麼氣勢。嚴重一點,口中涎流,嘴巴流口水。嘴巴流口水非常不好,你打坐的時候嘴巴流口水,你的身體太寒冷,溫度不夠,這個都是有問題了。
或時暗晦,明瞭性不夠。爾時應當斂身急念,令心住緣中,身體相持,以此為治。
這個時候把身體再振作起來,把念力再生起,專一地、相續地在所緣境當中去憶念你的佛號。這個是寬相的對治。
心有澀滑之相,推之可知。是為初入定,調心方法。
這個澀相,就是心中有一些罣礙。有些人他念佛念久了,他有罣礙,或者是很沉悶,這個時候你要想一些讓你歡喜的事情。
所以這個七覺支——喜,喜除澀,就是你想想你現在的辛苦,將來能夠到極樂世界,受用種種的正報、依報的功德莊嚴,想一些歡喜的事情,來對治這個澀,這個澀就是阻礙跟沉悶。
這個滑,就是心中妄想太多了,收攝不住了,這個剛好相反,要用收攝的法門來攝取。
推之可知,是為初入定,調心方法。
夫入定本是從粗入細,是以身既為粗,息居其中,心最為細靜。調粗就細,令心安靜,此則入定初方便也。是名初入定時調三事也。
入定的時候,是從粗到細,他先調身,把身體調好,再用吐納法把氣息調到深長而微細,這是調息。然後再調心,調到內心當中明瞭而寂靜,寂靜而明瞭,這個是我們在初入禪的調三事的方法。
我們菩薩的修學法門有六度法門,這個六度法門,一般把它分成兩類:
一個是佈施、持戒、忍辱,這種善法一般是講到凡夫的法門,就是說,你要去修佈施持戒忍辱,不需要什麼調不調,身息心都不需要調,你要做,就去做了。身體粗重,內心散亂都無所謂,只要有一念的善心,有一念的意樂就可以去做了。
這個禪定跟智慧這兩個法門,那是一個過人之法,就是超越凡夫的法門。就是說,這個止觀是怎麼回事呢?就是在你內心那個有漏的無明的心中,要栽培一個無漏的功德,這種修行的方式是逆生死流。佈施、持戒、忍辱還不能夠逆生死流,雖然你佈施,雖然你持戒,雖然你忍辱,你內心能夠生起善法,但是這個方向還是隨順於生死流,只是說,在一個生死當中成就一個善業,成就一個可樂果報,如此而已。
這個止觀就不是這種境界了,那是逆生死流,那是要解脫生死的一種功德。所以它的過程,它特別的複雜,身體要注意,氣息要注意,內心的狀態隨時要注意。因為它這個地方是一個大事,這是一個大事業,生死的大事業。
所以我們在前面說到:滿設恆沙界,珍寶供養佛,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寂靜。你用這個佈施波羅蜜滿設恆沙界,用恆河沙的珍寶來供養佛,這種功德比不上你在一天當中修習止、修習觀。因為你的滿設恆沙界的佈施,它不能成就解脫分,你用這個一日修寂靜,它能夠成就解脫分,它對於解脫生死,它有一分的功德力。你這個佈施、持戒、忍辱對於解脫生死是沒有功德力的,它只能是說是修止觀的一個基礎,所以這個地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