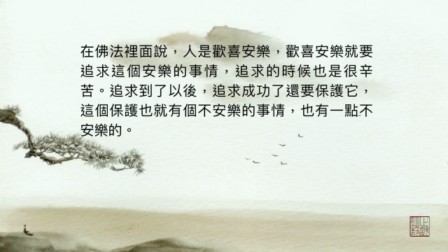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
持經利益隨心論,以今人受持經典,了無敬畏而發。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敬畏中求,能竭誠致敬,縱究竟果德,尚能即得,況其下焉者哉。餘皆隨事而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取其益,勿校其跡,自有裨益。倘以古德著作繩之,則將焚燬之不暇,何可令其一經於目哉。
在早期發表的論文當中,《持經利益隨心論》,是說我們受持佛經能不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跟我們能受持的人存什麼心是相關的,是談這個。那麼這篇論文的寫作緣起,是印祖觀察到現代人受持佛經沒有一點恭敬和畏懼。
印祖發現很多人把佛經放在桌面上跟那些雜物放在一起,看經典的時候毫無恭敬:躺在沙發上看,或者一邊挖鼻子、挖耳屎,或者摳腳板,甚至放屁,諸如此類。這些不僅得不到利益,而且是一種褻瀆。再就是,印祖常常看到一些居士乃至一些大文化人,拿著佛經,卷起來看、翻角,都要呵斥他,了無恭敬。所以有鑒於此,印祖從慈悲心裡面寫出這篇文稿。它也是末法眾生的特點之一。末法眾生是很難生起恭敬心的。上古時候人心淳厚,尊師重道,他那個恭敬心由衷而發。現在的眾生善根薄弱,人我是非,我慢嚴重,尊師重道就很難了。
當時佛說了一部《佛說正恭敬經》。阿難請問這個恭敬之法,佛開始都不跟他說。因為說出來,很多人、現代的眾生會害怕,他也做不到。阿難聽了之後發願他來奉行正恭敬法,來為末法的眾生做一個榜樣。那恭敬法裡面說到,一個學人對和尚阿闍梨講話都不能露齒;走路不能踩到影子;請法要跪著;出來,後退到見不到的地方再跪著;每天早晚要問安,如果和尚阿闍梨在裡面不理睬,要到門外再來頂禮三拜,然後繞屋三匝,再回去;和尚阿闍梨沒有說什麼你就不能去做,事事要請教;不能在背後說和尚阿闍梨的壞話,如果說了一句壞話,就要到地獄裡面遭受六十小劫的苦刑,等等。
這一說我們看得也膽戰心驚,我們做不到這種恭敬。那什麼叫阿闍梨?阿闍梨就是一個人跟你講過一四句偈,講過一偈法,講過四句法的人就是你的阿闍梨呀。現代人能做得到嗎?他聽了很多法,對法師、老師什麼的,一到下面,「哎呀,他講得怎麼樣、他講得怎麼樣,他哪如我呀!」馬上就說壞話了。他不知道這一出口就是六十小劫的地獄苦,所以這個很麻煩。
末法眾生是沒有這種恭敬心。沒有恭敬他就得不到利益,甚至未來的苦報有不堪設想者矣。所以印祖在很多文稿裡面,一段很有名的文句就是談恭敬問題:「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則消十份罪業,得十分利益。如果了無恭敬,雖種遠因,然其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也」。這個「不堪設想者」印祖都不敢把這個後果說出來,一說出來,那簡直就是沒有辦法說啊。但經典當中把這後果說得很清楚啊。所以為此,就寫出這部論出來,要在佛法當中得到真實的利益,一定要在恭敬、畏懼當中去求。得佛法實益的奧妙就是「誠」和「敬」兩個字。
「竭誠致敬」,古人對經典的那種恭敬,如果寫一部經,那不僅要香湯沐浴,要洗手,要換新鮮的衣服,每次寫字前都要沐浴更衣,甚至吐氣都有個管子通到屋外,摒住氣來寫。然後要吐氣的時候趕緊離開,再用一根管子通到外面去。寫經的紙有時候都是自己種樹,三年先種樹,這樹都是用很乾淨的泥巴,用香泥,香水,每天到那個種樹的地方都得沐浴更衣,然後持咒、梵唄。種三年樹一直很乾淨,從一開始就非常潔淨地做過來。寫一個字都要頂禮幾拜。
這樣寫出的經,一寫完這個經就能放光的。所以我們看到古人,他讀經之前一定要凝定心,先靜默若干時,然後再展開經本。展開經本想像佛就在面前,如對聖容。每部經的文句就是佛對我們親口而宣說,不敢有絲毫的念頭分散和輕慢之心。那寫經也是全神貫注,全神貫注也是他恭敬的表現。那全神貫注這種真誠、至誠就能感通。
有位古德在寫《法華經》的時候,寫到天黑了。天黑了,他的侍者進來,「唉?天已經黑定了,你怎麼還在寫啊?」等他一聽這句話,再一看,漆黑一團了。但是他寫經的時候恭敬至極、心無分別,他的筆下是光亮的。等到一分別,也就暗了、黑了。
所以印祖講,如果能誠敬到極點,就是成佛的果德都能夠得到,更何況其他伏煩惱、斷煩惱、開智慧、得福德也都能得到啊!他的《持經利益隨心論》很短。緊接著,他還有一篇將近一二萬字的《竭誠方獲實益論》,大家可以看一看。「竭誠方獲」,你真誠到極點才能得到真實的利益。
印祖在開示樂清吳璧華居士的時候,也是談這一點。吳璧華居士是早年留學日本的,他向印祖請教怎麼樣能夠修行佛法?修行佛法有沒有什麼秘訣?印祖就說,「修行佛法有秘訣,秘訣就是誠、敬兩個字。」這是玄之又玄的。所以這兩個字:誠、敬,舉世之人都知道,然而誠敬之道舉世之人都暗昧,都做不到。
就好像白居易居士去參訪鳥窠禪師,說「什麼是佛法大意?」鳥窠禪師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說「這兩句話,三歲小孩都道得出。」鳥窠禪師說,「但這兩句話八十老翁都行不得啊」。你能把諸惡不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做到究竟,那都成佛了。哪有那麼容易啊?所以這篇大家可以反覆去讀。那麼從這個開導可以看出,印祖希望周孟由兩兄弟,一定要在竭誠致敬方面去獲得佛法的利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山頭的石塊可以用來琢磨這個玉,這個意思就是說你不要以為我的話,就比喻他山之石,但是你能按這個話去做,也能雕琢你這個人才,雕琢成器啊。你就取這個文稿的利益,不要去計較這個文辭的粗糙,就自然會得到這個法上的利益。我這幾篇文稿,如果你以古聖先賢、古德的高論、宏篇、經義,這個標準來衡量,那我是遠遠不及。那我唯恐把它燒燬都不暇,趕緊要把它收回,怎麼可能還能夠經你們兩位大德的眼光去看呢?你不要計較它文字的粗糙,也不要跟上古的古德相比,相差甚遠的。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這篇文稿,你銷歸自性得利益,其他的你都不要去計較。我是一個凡夫僧,寫的東西也是不很高明,你不要計較這樣的跡象,自然有裨益。
所以這是印祖他在自己的文稿、文章裡面,一方面他謙虛,而謙虛裡面包含著他對於自己所闡述的義理,針對末法眾生的根機能令他得到利益,他有一種自信、自肯在裡面。也就苦口婆心地轉述,你們要好好地讀一讀這部論,依教奉行。那麼讀經、讀論,不像世間人要去考功名、考學位,佛法裡面讀所有的經論都要把他看成是教誨,看成是我們行為的指南。是要依教奉行的,是要銷歸自性的,是要落實在我們的行動當中的。
佛法的修行你不能在行動當中體現出來,它就沒有力量。你僅僅在文相、概念當中去兜圈子,縱然說得天花亂墜,縱然能夠寫出很多的文稿,著作等身,但是你內心的道力顯發不出來,於是在生死面前,在臘月三十到來的時候,都不能得到真實利益,手忙腳亂,還是「瞥爾隨他去」,「哀哉甚可傷」。
《復永嘉某居士昆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