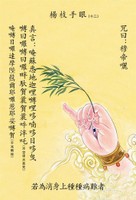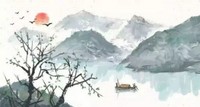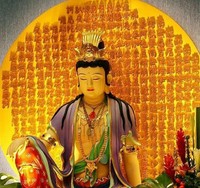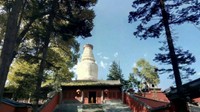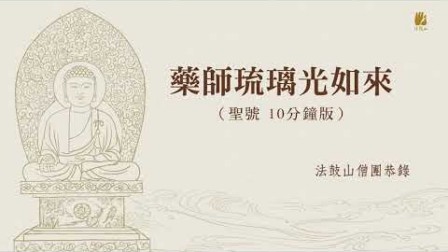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
俗話說「吃五穀生百病」,生、老、病、死是分段八苦的內容。在佛教中通常認為病有身病、心病之分。身病是由於「四大」不調,故而用「物藥」來治療,因緣所生法中有了病就去看醫生進行治療,有病不看則是外道,非佛弟子行為。
物藥有植物、動物、礦物三種,無非是為平衡「四大」,令身體輕安。如果是心病,或者是業障病,則要用「法藥」來醫。在聽聞佛法時,也要求聞法者把講法者當醫生想,把佛法當藥想,把依法修行當作治療想。
修行人所得的定慧功夫,在靜中練就十分,動中就只剩一分;在動中練就十分,在病中就只剩一分;在病中練就十分,在命終就只剩一分。可見在病中能夠提起正念用功,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就著維摩大士示疾的因緣,文殊菩薩就藉機問:「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也就是問生了病後應該怎麼用功修行。維摩大士所作的一番開示,也有益於我人在病中用心。
大概意思有三點:生病以後,首先不要怨天怨地,應該先從事相上,也就是從佛法因果觀中心生懺悔,反觀這個生病的因緣,是由於過去世妄想、顛倒、煩惱而生,由迷惑而造業所感的果報。
其次從理上觀照,這個病是虛幻不實的,因有我,才有我所生病,而我的真實寫照只是地水火風四大的假合,四大本來就是無主的,何處有我?由於有我,才有我生病,現在我都不存,病將何寄!
既然知道病根是有我,就要破除下意識執身為我的思維,我只是四大五蘊之法和合而成,實際上生滅也只是法在生滅,聚散也是法在聚散,何來有我,既然無我,誰在生病。
第三從發心上而言,當我人有病苦時,憶念一切眾生都會受到病苦,以及惡道眾生猶如常病常苦,發心救度一切病苦眾生,代一切病苦眾生受苦。
再進一步而言,維摩大士說因眾生貪愛,故他有病,從根本上說明有求皆是病苦,所以餓了就是病,飲食就是藥;困了想睡就是病,床榻就是藥;感覺到冷的時候,烤火就是藥,烤火過了頭,著火就是病,凡一切眾生所需皆是病,能滿一切眾生所需皆為藥。縱觀因緣中,就沒有一個絕對的病,也沒有一個定性的藥。所以《華嚴經》中普賢菩薩讓善財童子入山採藥,他空手而歸,說滿山無不是藥;次日讓他把非藥採回來,善財童子又空手而歸,因為滿山遍野皆是非藥。
最後維摩大士說,生病的行者應當以「無所得」調伏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