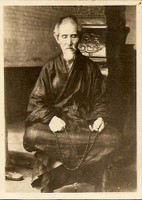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
今天給大家講的題目叫「無門關」。我想進入這個關、禪的關,連門都沒有,那麼說的一切都是多餘的。因為「凡有言說,都是虛妄」,言說只能是一種描述,它絕對不能真正接觸到禪的實質,所以「無門關」很難講。為了要描述這個禪,為了使我們通過語言符號對「無門關」的意思獲得些微的了解,我就在無說的基礎上、在無說的前提下畫蛇添足,來給各位作一點點介紹。
首先說說這個「無」字。「無」既是佛教哲學、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國儒道哲學裡的最高境界。中國的儒道哲學所謂「大道無門」,而佛教哲學是把一切萬事萬物最初的起源都歸納到「無」字上面。「無」字是梵文裡開始的第一個字「阿」,在密宗裡面是說「阿字本不生」[注1]。因為一切的萬法都是因緣所生,每一法都是眾緣和合。每一緣又是由眾緣和合,眾緣又有眾緣,眾緣還有眾緣,一直可以追溯到無始,找不到一個開頭。我們就隨便拿此一會來做一個例子。我們為什麼有這一次講經的法會?就從緣來分析,一直可以追溯到釋迦牟尼那靈山一會。再從佛的靈山一會往前追,那就追溯到佛的三大阿僧祇劫[注2]的修持行道度生,可以說叫前前無始。
我們又以這個法會作為一個點,再往下去追求,由此而產生各種影響,一個一個地向後推求,也可以說是後後無終。一件事是這樣,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無不如此。每一件事情都是前前無始——找不到它的開始,後後無終——找不到這件事究竟在什麼時候結束,哪裡是它的終點。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佛教就說一切法無生,因為追不到它的起點和盡頭在哪裡。這是佛教的觀點。
其它宗教認為世界上的一切萬事萬物有一個開始。這個開始是什麼呢?印度的婆羅門教就說是梵天[注3]創造,那就是個開始。至於梵天是誰創造的,就不能夠再往下追。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認為一切萬事萬物也有個開始,是上帝創造的。那上帝又是誰創造的呢?不能夠再去追問。這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聽過一個小故事,說在美國的學校裡,孩子們上有關宗教比較學的課。在學了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的一些基本道理之後,老師出題問佛教和基督教有什麼不同,這是一個思考題。
美國的孩子答得很簡單,他們說佛教認為第一個雞蛋是雞生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認為第一個雞蛋不是雞生的。這個答案很生動很巧妙地把問題解決了,佛教與基督教、天主教的不同就在於此。因為基督教和天主教認為第一個雞蛋是上帝生的,不是雞生的。而佛教認為第一個雞蛋還是雞生的,一直可以追到前前無始、沒有一個開始的地方,所以叫「無始終,無內外,強立名,為法界」。我們佛學院的學生都讀過《佛教三字經》[注4],開頭的幾句話就是這樣講的,講一切事物就是這樣。
「阿字本不生」的「阿」字,翻成中國字就是「無」。無者就是般若的最高境界,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我們佛教歷史上有一位最有名的佛學大師叫僧肇,他寫了四篇論文,其中就有一個《般若無知論》。般若本來是真知,本來是最高的智慧,他說「般若無知」就是用「無」來概括佛教的最高智慧。
我們不要隨便地給「無」字來一個定位,不要認為是有無的「無」,無就是沒有,不是這個意思。「無」在這裡就是般若理論所主張的「空」。大家都知道三論宗的《中論》,裡面有一首偈子寫道「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正是有「無」,所以一切法才得成。這個「無」是指什麼呢?「無」是指一切法無自性。每一個法都無自性,所以它都能夠成為另一個法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如果每一個法都有自性的話,它就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互不合作。正因為它沒有自性,可以隨意地組合,說這種組合是隨意的僅是我們一般的看法,這種組合也體現了「法爾道理」[注5]。
我們人生存在這個環境裡面,很巧啊,鼻子都朝下,耳朵就長在兩邊,眼睛就會看東西,肚子餓了要吃飯。這些問題當然要用科學來說明好像也說得清楚,但實際上那種說明是很勉強的。究竟它為什麼要長出這樣一個樣子來?法爾如是。佛教認為這都是法爾的,它就是應該這樣,不能夠是第二樣。像這樣的一些東西,這樣的一些道理,這樣的一些現象,應該說佛教回答得最有智慧。它把它們都歸納成為緣起而性空這樣一個最高的哲學理念,或者是以「無」來概括它。
我們大體上把「無」字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和價值,乃至在中國老莊哲學裡面的重要地位這樣一個重要內容,給大家作了一番簡單介紹。下面就講「無門關」。
「無門關」的來歷是什麼呢?各位看過禪宗公案的人都知道趙州和尚的一個著名公案。有人來參拜趙州和尚,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問道:「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狗子有沒有佛性。趙州和尚就說:「無!」狗子沒有佛性。那個參拜的人進一步地問:「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為什麼狗子就沒有佛性呢?」趙州說:「因為它有業識在。」這是一個公案。
我們有一點佛教常識的人來判斷這個公案,肯定說趙州和尚的回答是和佛教常識相違背的。因為佛教常識都講,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嘛,狗子為什麼就沒有佛性呢?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忘記,這個「無」不是有無的「無」,是超越了對立的「無」,這個「無」是在給你一個思路。按照通常情況,你的思路會往前繼續去想、繼續去追這個問題。但是趙州和尚的回答就好像閘門關下來一樣,一下子截斷了你思路的水流,一下子將你的思路堵塞了。思路堵塞以後,你的前面就好像壁立萬仞,無路可走。也可以說一下子把你推到萬丈懸崖的邊沿,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會掉下去。如果那個時候能夠掉下去,那就是禪宗講的「撒手懸崖」,就可以真正地超越。禪宗的功夫就在這個地方,就是在你問答之間真正能夠契入,一下子把你的思路堵住了,你不要再繼續往前閃。一下子壁立萬仞,你再找一個出路、找一個翻身的地方,你就算無門也能進去。如果你還在知識裡面兜圈子的話,那你永遠都沒有一個入處。
這裡還有一個公案,是五祖法演[注6]禪師講出來的一個公案。這個公案聽起來好像是很俗,但實際上非常有味道。禪宗是要你從沒有門的地方能夠進去,你能夠得一個轉身、能夠翻身,那才是本事,這個公案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說有一位做盜賊的父親養了一個兒子,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盜賊老子總是帶著兒子一起做盜竊的事。他們那時不像現在撬鎖偷荷包搶銀行,古今做小偷的各有各的辦法。古代是挖窟窿。你在房子裡面,他要偷你東西就先在牆上挖一個窟窿鑽進去,我們這些老年人都知道這種事,年輕人就不知道,年輕人只知道做小偷要下門下鎖。古代在農村裡是挖一個窟窿,然後鑽進去。盜賊的兒子長到十七八歲了,他說:「父親啊,你天天帶著我偷東西,我老跟著你做,將來萬一你不能動了,那我怎麼辦啊?你總要把絕活教我一兩招,好讓我以後也能獨立謀生。」父親聽到兒子這麼說非常高興:噢,他還想獨立地去偷盜呢,那說明他有出息。
父親也不說他哪一天會教兒子,還是照樣把兒子帶到外面。有一天他們挖到一個大戶人家裡去了,父子兩個都到了屋裡,屋裡有一個衣櫃。過去的衣櫃不像我們現在這樣,過去的衣櫃很高,放東西要打開了進去。父親輕輕地把一個衣櫃打開,叫他兒子去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兒子朝衣櫃裡面一走,父親就把門一關,然後把他鎖在裡面。鎖了衣櫃以後,父親就從挖的窟窿跑了出去,又弄一捆荊棘把洞口給堵住。他再到外面喊主人家的門,說他家裡有盜賊,讓他們趕快起來捉賊。用禪宗的話來說,這是把這個兒子置於死地,看他在這個時候能不能找到一個翻身的機會。他兒子這一下急了:啊!他今天怎麼跟我來這一招,這不是明明要把我置於死地嗎?這個時候,他心裡在想怎麼樣逃脫困境。他先在櫃子裡學老鼠叫,這家人聽到櫃子不停地在響,家裡的老太婆就點上燈慢慢地把櫃子門打開。
一打開,這個小盜賊就把燈吹熄了,然後拚命地往外跑。他跑到洞口想鑽出去,見有一捆刺把洞堵得死死的。在這個時候,剛好洞旁邊有一個馬桶,這個兒子就把馬桶裡的東西倒得乾乾淨淨,朝頭上一罩,一下子就鑽出去了。鑽出去是死裡逃生,但是後面的人還是追來了。追到前面不遠有一口水井,水井旁邊又有塊石頭,他看到後面的人追來以後,就把石頭丟到水井裡面去,發出很大的聲響。晚上模模糊糊的,人家以為這個小盜賊跳到井裡淹死了,而他一溜煙就跑掉了。這個兒子跑回家以後,就責問父親:「你今天怎麼這樣來整我?你這不是要我的命嘛!」父親問他是怎麼出來的,他就把經過向他父親講了一番,還是滿口的抱怨。他父親說:「好了,我的絕招已經教給你了,這就是絕招。」
參禪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一定把你推到無路可走的地方,讓你自己去找一個翻身的機會,那樣你就能開悟了。這個故事雖然很粗很俗,但是我們要逃出生死、要真正得到解脫,故事所蘊含的道理還是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的。所以說「無」字的作用就在這裡,它不讓你有一個思考的餘地,禪宗許多公案都是如此。
趙州和尚還有一個公案叫做「祖師西來意」。達摩祖師從印度到中國來究竟傳的是什麼法,他的宗旨是什麼。這是禪宗千古以來的一個大問題,一直被人們所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關於這個問題,可能有一千種以上的答案。那麼趙州和尚的答案是什麼呢?人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和尚說:「庭前柏樹子。」你說庭前柏樹子和祖師西來意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我們從知識的層面去理解,簡直是答非所問。但是真正懂得禪的人會覺得這種回答才真正是祖師的苦口婆心,他是讓你好好地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自己去找一個入處。
還有的祖師問如何是佛。有個祖師就問洞山禪師:「如何是佛?」他說:「麻三斤,布一匹。」他說這就是佛。你說麻三斤和布一匹怎麼和佛聯繫起來?也是一樣的道理,就是讓你不要在知識上去分別,把你的思路一下子給切斷。切斷了思路以後,在壁立萬仞的情況下,你的思想往往會有一番新的境界出現。我們一些搞文學創作的人、寫詩的人往往也能夠有這樣的一種體驗,但這種體驗對他們來講只不過是石火電光一閃而過。不能夠持久,不能有真正的思想上的昇華與飛躍。
由趙州和尚「狗子無佛性」這個公案直接就引出了「無門關」,「無門關」是禪宗最高的一種悟的境界。有人參這個公案,參了之後,這個公案就廣為流傳,然後它才成為一個案例。好像是我們審案子一樣,審案子不可能每一案都一點點地去分析,他總有一個參照的案例。禪宗的公案也是如此,它也基本上被定型,關於定型的禪宗公案的書有很多。
公案到了宋朝的時候就叫「古」。有時候我們鄉下的人,特別是我們湖北人,管講故事叫「款古」,講一個故事聽就叫「款一個古仔聽」。廣州人也把故事叫「古仔」,說「款一古仔聽一聽」,公案後來也叫「古」。
有很多禪師作詩偈頌古,就是把公案用四句話、八句話來描述一番。北宋時期雲門宗有一個祖師叫雪竇重顯[注7],他選了一百則公案進行讚頌,叫《頌古百則》。隨後有個臨濟宗的禪師叫圓悟克勤[注8],他根據《頌古百則》一一加以解釋、描述和評論,就叫評唱。然後把書取名為《碧岩錄》,或者叫《碧岩集》。這個碧岩就是湖南夾山靈泉禪院牆上的「碧岩」二字,是那時靈泉禪院方丈的名字。這個方丈不是叫方丈,叫碧岩。為什麼叫做碧岩呢?靈泉禪院的開山祖師叫善慧禪師,他有兩句詩描述他的悟境:「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岩前。」後來有人覺得他這句詩有「碧岩」二字,就把這兩個字單單拿出來作為方丈的名字。圓悟克勤正是在那間屋子裡集成這本書,所以把書叫做《碧岩錄》。
《碧岩錄》這本書在當時的禪門被稱作「禪門第一書」,所有住禪堂的人、參禪的人都要人手一冊。沒有刻印本,抄寫也要抄一本。《碧岩錄》是非常有名的書,因為雪竇重顯是一位悟境很深、文學修養很高的大禪師,他的文字非常優美,他的《頌古百則》在悟境上是高超的,在文字上也可以說是第一流的,所以受到當時禪人的重視。圓悟克勤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禪師,他的評唱文字也非常優美,所以說這書在當時非常流行。這本書一流行以後往往就流入「文字禪」,人們不去參悟,專門書上找四言八句來跟你說一說對一對,這就成了「文字禪」,或者說「葛藤禪」。圓悟克勤有個弟子叫大慧宗杲,他看到這種情形會瞎天下人眼目,就一下子把《碧岩錄》的版毀掉了,不准這本書再流通。徒弟對師父下這樣的毒手也是不簡單的事情,要是我們現在的人,還不說你大逆不道?!但是他當時就把版給毀掉了。過了若干年以後,這本書還是重新刻版流通。
《碧岩錄》是臨濟宗一本關於公案的書,有一百則公案。曹洞宗有一本書叫《從容錄》,也是一百則公案。這兩個一百則公案,往往有重複的地方,但是它們的思路不同。臨濟宗叫「看話禪」[注9],曹洞宗是「默照禪」[注10],他們兩家的思路不同,對同一個公案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這兩本書裡面都選了趙州和尚「狗子無佛性」這一樁公案。
大概過了一百年以後,臨濟宗又出了一位祖師叫無門慧開,他在這兩本書的基礎上,重新提煉出四十八則公案,四十八則公案就叫《無門關》。《無門關》的第一則公案就是「趙州狗子」。無門慧開在這裡有幾句非常精彩的話,他說:「參禪需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只這一個‘無'字,乃宗門第一關也。遂目之日,禪宗無門關也。」「無門關」就是由此而來。這段話是說,趙州狗子無佛性公案裡的「無」字就是禪宗的一關,參禪開悟就是要以「無」為門,無門就是門,一定要有這樣的一種精神來對待參禪這件事。
《無門關》這本書寫出來以後也受到禪門的重視,特別是它流傳到日本以後,可以說一版再版,一刻再刻,經常有人來研究、提倡這本書,中國的禪門對這本書好像都不知道了。最近這幾年台灣有人在研究這本書,那也是在日本人影響之下才重視起這本書來的。除了日本重視它以外,現在禪宗傳到西方歐美,各國很重視《無門關》這本書。這本書不但有英譯本,連匈牙利那麼一個小國家都根據英文把它翻譯成匈牙利的文字。1997年我到匈牙利去的時候,那裡有一個佛教的學校,我在那裡看到有一本書全是匈牙利文字。我是一個匈牙利文字都不認得的,但是書上面有一個漢字「關」。那個字是日本古代禪師寫的一個字,匈牙利人就把它印在那本書上面,用匈牙利的文字寫了「無門」,然後用日本人寫的一個「關」放在那上面,還是「無門關」。我就問他們,這本書是什麼,他們就向我介紹說這是《無門關》。唉呀!我心裡一想,我們中國人太慚愧!中國人太慚愧!對自己祖宗的東西沒有真正地去認識,而這本書在海外受到如此重視。
這幾年我在柏林禪寺多次主持禪七,不免要牽涉到趙州和尚的很多公案,其中就包括這個「無」字公案。晚清以來,真正參「無」字公案的人很少。明以前都參「無」字公案,明以後都參「念佛是誰」這個公案。因為禪和淨土基本上結合起來了,所以祖師們沒有辦法。你在念佛、念阿彌陀佛,念佛的是誰呀?你跟我說一句看。這樣就有一個「念佛是誰」的公案出現。最古老的還不是「念佛是誰」,最古老的是「無」字公案。
日本禪宗是沒有「念佛是誰」這個公案的,他們參的還是「無」字公案。1992年,我們柏林寺普光明殿開光時就請了日本臨濟宗的一位禪師來參加活動。活動結束後,這位日本禪師就到趙州和尚塔前去拈香禮拜。拈香禮拜完了,他要說四句偈子,叫香語。我們現在中國人都叫法語,日本人、韓國人叫香語。他拈香說了四句香語以後就大喝一聲,大喝什麼呢?就是那個「無」字。那個「無」字聲音一喊出來呀,驚天動地,他底氣非常足。他就是福島慶道[注11],可能也到玉佛寺來過,他懂日文、英文,能夠用英文講禪。他那個「無」字一喊,好像屋上的瓦都會被震動下來,就有那樣的底氣。日本人的禪還是根據「無門關」、根據「狗子無佛性」的這個「無」在參究。
日本人在題字的時候,他會寫三個字「州雲無」。「州」就是趙州,「雲」就是說,底下就是「無」字。因為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他就寫這麼三個字給你,前面的話都不要,就是「州雲無」,這很有禪味。
作為出家人,我想一定要懂一點禪,或者說一定要從禪這個方面打開我們的思想境界,這樣才有靈氣,才不會流於膚淺。因為禪是很深沉的東西,是很內向的東西,參到了家,它又是很開放的東西。不管深沉也好、內向也好、開放也好,它都有那個味道。
「無門關」的來歷就是如此。下面我講一下究竟該怎樣來修這個「無門關」,究竟怎樣來參究這個「無門關」。提倡修「無門關」最有名的應該是宋朝的大慧宗杲,在他的語錄裡面有多處開示怎樣修「無門關」。關於我們怎樣面對這個「無」字,他說,我們不能夠把「無」當作有無來會,不能把「無」當作虛無來會,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不能從知識的角度去理解。他一共從八個方面來說明我們在參這個「無」字的時候應該怎麼樣去避免像常識方面的一些理念。他說,要把「無」當作一個生鐵鑄成的丸子,然後你就去咬它。這個生鐵鑄成的鐵丸一點滋味也沒有,但沒有滋味你還要去咬。咬來咬去,最後要把這個鐵丸咬破,咬破了這個鐵丸就說明你到家了。
這說明參「無」字的時候難度是很大的,這是一個比喻。還有一個比喻也是很粗的,他說,就像狗子碰到一塊熱糍粑,它一口咬過去,咽又嚥不下,吐又吐不出。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要找一個辦法從困境中解脫出來。第三個比喻就是剛才說的那個小盜賊的故事,人家家里人都起來捉賊了,怎麼從堵著荊棘的洞口鑽出來,在完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找一個出路。這就是禪的精神,這也就是「無」的精神,我想這也是我們修行的精神。我們修一切法門都要有這種精神才能夠真正得受用,才能真正見效果。無門既然是一個關,我們學佛修行也是一關,想突破這一關非要下大力氣、大決心不可,非要拚搏一番才有可能大死中求大活。
下面我們再從「無」字的角度來看看它在佛教裡面真實的意義。這幾天在講禪的時候都涉及一個問題,就是都涉及到知識的層面和實相的層面,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呢?比如說我現在在喝茶,諸位也看見我在喝茶,但喝的感受與看的感受是兩碼事。首先人家會有一個問題,他喝的是什麼茶,然後,茶的滋味是什麼,茶是涼的還是熱的……,就有一連串知性上的問題在腦子裡打轉。這是從觀看的角度來說的。那麼喝茶的人有沒有這些問題呢?沒有。因為他是直接地接觸了茶,他自己完全能夠明白茶是什麼味道。這就叫「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冷也好暖也好,這個「冷暖自知」是事物的本質,事物的自相。我們現在在了解事物的時候都是在事物的共相上面進行了解,共相是知性上的東西,自相才是事物的實質,是事物法爾上的東西,事物的當體。要了解任何一個事物,就要了解共相的東西,這使我們能夠把握一切事物共同的特點。但是真正要了解每一個具體的事物,那必須要了解它的自相,也就是說要了解事物的個性。不僅僅是要了解事物的共性,而且要了解它的個性,個性是此一事非彼一事。
共相只能掌握一切事物的平等性,自相才能了解一切事物的差別性。這個事物和那個事物之所以不同,是由它們的差別性所決定的。張三和李四各有名稱,你籠統地喊「人」,張三不會應你,李四也不會應你,因為那個「人」是共性。只有把他的自相差別性分辨出來,你喊張三,張三會答應你,你喊李四,李四會答應你。這就是諸法的自相或者差別性,當然兩者之間——平等性與差別性,自相與共相,個性與共性——也不能完全分離,但是要了解事物,自相非常重要。
自相和共相,體現在法爾道理上不可言說的東西都是自相,是我們直接接觸的事物,是不可言說的。這個不可言說的東西只有用「無」、用一些代名詞才能夠表現出來。這種法爾道理往往連佛也不說,他怎麼說呢?「法爾如是」,「有佛出世」,「無佛出世」,「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他也只能夠用這樣的話來表示。因為如果你在每一事物上把它無始無終的東西一點一點地來推敲,那就要犯一種無盡的過。你說法沒有辦法說,寫書沒有辦法寫,說話也沒有辦法說。對每一件事物的了解也是一樣,那也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囉嗦。所以一切是法爾如是。
我們說佛是全知全能,但是佛自己說,「佛有七能三不能」。有他不能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有他無奈的地方。比如說眾生界不可窮,眾生的業力不可窮。佛陀說要把眾生度盡,眾生盡得了盡不了呢?佛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也是無奈的。為什麼呢?眾生每個人有自己的業力。因為業力不同,所以眾生的流轉生死也不可能在一天都往生極樂世界,不可以在一天同時證得涅槃。面對這樣的事情,佛也感覺到無奈,只得說「佛不度無緣眾生」。因為這些眾生的因緣還沒有成熟,他的業力還要繼續流轉。這也是一種法爾道理,這種道理也是「法爾如是」。每個人只能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佛只能告訴你一個方法,你不採納這個方法,佛也拿你沒奈何。就像你有病醫生讓你吃藥,你拿了藥回來又不吃,醫生也拿你沒辦法,醫生面對不合作的人也無奈。所以在佛經裡對這個法爾道理講得很多。
有一位日本的白隱禪師[注13],是16到17世紀時候的人。他有一首詩,就是描述法爾道理,描述這個說不出來的東西,描述物質所包涵的這樣的一種境界。他寫道:「畢波羅窟裡,未結集此經;童壽譯無語,阿難豈得聽。北風吹窗紙,南雁雪蘆汀;山月苦如瘦,寒雲冷欲零。千佛縱出世,不添減一丁。」大家知道,第一次結集是在印度畢波羅窟,由五百阿羅漢結集三藏。白隱禪師說,這個法爾道理,像這個「無」字所包含的這本經,在畢波羅窟裡面沒有結集出來,因為它是語言文字所不能表達的。童壽就是鳩摩羅什,鳩摩羅什翻譯成中國話就是童壽。童壽要翻譯這本經典也沒有語言可以表達,所以「童壽譯無語」。第四句是說阿難也從來沒有聽佛說過這本經,因為這不是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的,是言外之意,「童壽譯無語,阿難豈得聽。」
下面就講法爾道理的種種現象。比如說「北風吹窗紙」,北風起來吹到窗戶紙上,一響一響,陣陣寒風吹過來。這種道理能夠描述得出來嗎?描述不出來,這種情景就是法爾,當然我們現在用紙來糊窗戶的已經很少了,農村裡可能還有一點,城市里都是大玻璃窗。北風起來吹窗戶紙是北方的情景,而南方是「南雁雪蘆汀」。雁是白色的,它落在蘆花一般的河灘上,就好像是一片白雪一樣。這是什麼道理?為什麼雁就是白的?你要說是說不出來的。「山月苦如瘦,寒雲冷欲零」。山上的月亮出來既冷而且又好像是非常地清靜,非常地寂寞,那樣的一種情景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能夠去會體會。天寒地凍的時候,看到天上的雲彩在那裡飛,好像一片片的雲彩馬上要從天上掉下來一樣,就是「寒雲冷欲零」。這些都是法爾道理,它為什麼像這樣?人們怎麼樣去分析它?即使分析出道理來,你也把它無奈何。你也只能夠讓它就這樣,你再不能夠有第二個方法去改變它。所以接下來白隱禪師用兩句話來結束他這首詩:「千佛縱出世,不添減一丁。」縱然千佛出世,對法爾的道理也是既不能增加一點,也不能減少一點。所以說千佛出世也要認同法爾道理、也要認同「無」所表現的境界,他們也會印證這個事情,認為這是諸法的實相——「諸法實相義」嘛。
今天講這個「無門關」,實際上是用語言文字描述「無」的境界,不是「無門關」就是如此?不見得。因為「凡有言說,皆是虛妄」,都是在虛妄分別當中。虛妄分別的東西往往也有一點點的作用,就是可以像用指頭指月亮一樣。如果我們能夠不止於指,直接見月,由一指指月還是有作用的。如果有人以指為月,就是害了大家,以為這就是「無門關」,非也非也!「無門關」需要我們來參,需要我們來悟,需要我們從壁立萬仞的牆上找到一個可以進去的縫隙。
==================================
[注1]密教謂「阿」字乃一切語言、文字之根本,含有不生義、空義、有義等多種意義。本不生者,本來本有,非今始生之義,是為阿字之實義。《大日經》卷二曰:「云何真言教法?謂阿字門,一切諸法本不生。」
[注2]三大阿僧祇劫為菩薩修行成滿至於佛果所須經歷之時間。阿僧祇,意為無量數、無央數;劫,為極長遠之時間名稱,有大、中、小三劫之別。三度之阿僧祇大劫,即稱三大阿僧祇劫。於三大劫中,釋迦佛值遇無數佛。
[注3]梵天音譯為婆羅賀摩、沒羅含摩、梵摩,意譯為清淨、離欲。印度思想將萬有之根源「梵」予以神格化,為婆羅門教、印度教之創造神,與濕婆、毗濕奴併稱為婆羅門教與印度教之三大神。通常所稱之梵天大都指大梵天王,又稱梵王,名為尸棄或世主。印度古傳說中,為劫初時從光音天下生,造作萬物,佛教中則以之與帝釋天同為佛教之護法神。
[注4]為明朝吹萬老人著,印光大師修訂,見附錄。
[注5]四種道理之一,其餘三種為觀待道理、作用道理、證成道理。謂有生必有死,有因必有果,乃天然自然之道理。
[注6]法演(?~1104),北宋臨濟宗楊岐派僧,晚年住蘄州五祖山東禪寺,世稱「五祖法演」。法嗣頗多,以佛眼清遠、太平慧勤、圜悟克勤最著,有「法演下三佛」之稱。
[注7]重顯(980~1052),北宋雲門宗僧。因在明州雪竇山資聖寺大揚宗風,又以師久住雪竇山,後世多以「雪竇禪師」稱之,為雲門宗中興之祖。
[注8]克勤(1063~1135),北宋臨濟宗楊岐派僧。於五祖山參謁法演,蒙其印證,與佛鑒慧勤、佛眼清遠齊名,世有「演門二勤一遠」之稱,被譽為叢林三傑。因高宗賜號「圓悟」而為世稱「圓悟克勤」。弟子有大慧宗杲、虎丘紹隆等禪門龍象。
[注9]又作看話頭、話頭禪,係臨濟宗僧大慧宗杲所提倡的宗風,即以參看話頭(古則、公案)為門徑的參禪方法。此禪風先慧後定,與默照禪先定後慧大異其趣。又,由於其中設有參禪機關,故又名機關禪。此外,由於是依次參究其他公案,故俗稱為梯子禪。
[注10]為宋代曹洞宗之宏智正覺禪師所倡導之禪風,主張以「坐空塵慮」來默然靜照,兀兀坐定,不必期求大悟,唯以無所得、無所悟之態度來坐禪。
[注11]福島慶道,日本臨濟宗十四派之一的東福寺派大本山東福寺管長,日中臨濟、黃檗宗友好交流協會會長。
[注12]白隱慧鶴(1685~1768),日本臨濟宗僧,字白隱,號鵠林。世稱臨濟宗中興之祖,或現代臨濟宗之父。生平提倡講演,以盛弘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