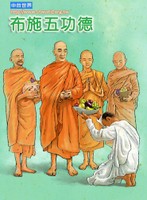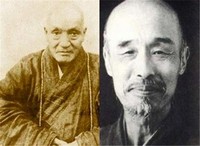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
我二十三歲的時候,在開縣大覺佛學院教書,那時,剛從漢藏教理院畢業沒多久。我在漢藏教理院是十六歲入學,到二十一歲畢業。在漢藏教理院,我聽過喜饒嘉措、法尊法師講關於西藏中觀論、印順法師講「三論」、雪松法師講「唯識」(如《解深密經》、《楞伽經》、《攝大乘論》、《成唯識論》和「因明」)。但那個時候當學僧,理解力強,慧通力不夠,同時呢,只重「解」不重「行」。所以,雖然學了這麼多東西,實際上不論在理解還是融通方面都還較差。另外由於忽略行持,沒能做到「解、行相應」。
到了開縣以後,由於法尊法師、雪松法師對我教育很切,太虛大師對我希望很深,於是自我策勵起來,白天講課,晚上讀經到深夜。我晚上讀的經典包括《大般若經》、《瑜伽師地論》、《大般涅槃經》、《大智度論》,還有《華嚴經》、《法華經》等比較大部頭的經論我都讀了。《大般若經》我也是利用晚上讀的,前後讀了半年時間。
我當時在大覺寺是住在那個藏經樓上。那個藏經樓是由曾在開縣住過的一個廖師長募款修建的,因為原來的藏經樓被火燒了,廖師長是個護法居士,就募資重建。這個藏經樓就修在廟後的一片荒坡之上。這片荒坡正好是過去舊社會講的棺山,孤墳累累,修的時候挖出很多白骨,就在這附近修一座很高大的塔,把這些白骨埋起來,叫白骨塔。因此藏經樓修好以後不清淨。
當時我們佛學院的講堂就在藏經樓。佛學院分為研究部和普通科,研究部的學生都住在藏經樓,普通科就住在廟上。另外有幾位教師,包括英語教師都住在藏經樓。他們經常在晚上聽到鬼叫,聽到狗叫。老師們都不敢在那裡住了,學生也嚇得跑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搬到那裡住下來。我住下來以後,可以說每個晚上都很安靜,沒聽到什麼,也沒看到什麼。我當時當教務主任,白天講課,晚上讀經。我在那裡晚上拜觀音菩薩,讀經,念《金剛經》,我覺得沒有什麼,很安靜。
我讀《大般若經》就從頭年的秋末經過冬天,到第二年的初夏才把它讀完。在讀完的那天晚上,天氣很好,月光很亮,很清淨。要讀完的時候,我就聽到窗外有腳步聲,踢踏踢踏的,我沒管它,繼續念我的,一心念,接著又響起第二次,最後我快要念完了,又響起第三次,我念完就出去看,是哪一個人在外面?結果一個人都沒有。天空的月色很明朗,一片清淨。當時我就想到有些公案:當大經讀完以後,往往有孤魂野鬼求超度。我想,一定是求超度。最後我就迴向,以讀經的功德使孤魂都能聽藏經往生。這以後就再也沒聽到什麼動靜。這是一個感應。
第二個感應。當時我晚上睡覺已經是半夜了。在夢中,客堂師父來給我傳達,說現在重慶有個貴客來會你。我聽說後馬上到了客堂,見到有一個中年人長得很端正,戴著禮帽,穿著長袍馬褂,那種舊社會的禮服,很清淨的樣子。
我走到他跟前,他馬上站起來,說:「法師,您請坐。」我就坐下。
他就跟我講:「現在我們請您到重慶,重慶有事情等您,您務必立即動身。」
我當時就答應:「可以嘛。」
他說:「現在您就上馬,那個馬兒拴在小山門外。」我就跟著他到了小山門,看到旁邊拴著一匹馬,很高大雄壯。小山門外就是一條很寬的石板路,一直通向山下。
那個人就跟我說:「請您上馬。」
我從來沒騎過馬的,但那個時候卻很會騎,翻身就踏上馬鞍。那個人一揮鞭,這個馬就踢踢踏踏起來,夢中都聽得很清楚。從大石板路向外跑,跑出山門以後,馬兒就四腳騰天,衝向天空,我一點兒也不感到恐懼,就隨著馬奔馳。馬衝向天空就向東方,飛向東方的過程中,就迎面看到一輪太陽,陽光四射,非常燦爛。這是早晨的太陽。太陽之光照耀山河,一片光明,此時我內心覺得很歡喜。就在歡喜的心情中,夢醒。
第二天我就把這個夢境告訴雪松法師。雪松法師給我印證,說:「這是你讀了《大般若經》後得的感應,是很好的象徵。騎馬是伏意馬,修行要伏意馬;騰空是修空性,空代表般若;修般若就可以啟發智慧光明。修行就是這麼一個次序。」
伏意馬、修空觀、發慧光,修行就是這麼一個過程。的確從此以後,我的智慧大大提高。以前讀書雖然有點一般的理解,但是融會不通。為什麼佛一會兒說 「有」,一會兒說「空」呢?一會兒說很多法門,一會兒又否定呀?大、小,空、有,融會不起來。雖然求了很多年的學,聽了很多課,但始終不能通達。自讀《大般若經》以後,可以說對於其它所有經典、教義基本上就能融會貫通了,再把以前所學的回憶起來,加以比較、鑒別、貫通,自己就有心得,體悟也很深。
這就是我讀《大般若經》的感應事蹟,希望大家能夠珍惜機會,堅定對般若修學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