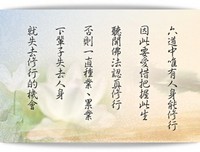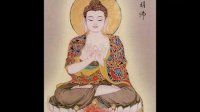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一個寂寞的人,雖能引起他人的同情;但人之對於寂寞的境遇,總是容易引起哀傷的情緒。所以寂寞的境遇,總是不受一般人所歡迎的。
但是,人而真正能夠忍受寂寞,安於寂寞,樂於寂寞,並且願以寂寞為其終身之良友者,他將必然通過寂寞之路,透出於寂寞的氛圍之外。他將會在寂寞之中,認識自己,認識他人,認識世間,認識世間的一切有情與無情;他將會發覺自己的缺陷,他人的缺陷,世間的缺陷,乃至一切有情與無情的缺陷;缺陷之中,產生憂患,憂患則與痛苦俱來;自己有痛苦,他人有痛苦,一切的有情眾生皆有痛苦;因為自己有痛苦,自己是人,凡是人,必皆有痛苦;又人是有情的眾生,凡是有情的眾生,亦當皆有痛苦。自求解脫痛苦,故亦必能逐漸而發為救人救世的大悲精神。到此境界,吾人的人性,已從孤單與寂寞之中,昇華而至於廣大無際的無盡藏中,自己深入於民胞物與的無盡之藏,自己的心胸,亦將充塞於無盡之藏,並進而彌蓋涵容了無盡之藏,此真所謂廣大如虛空了。但是,虛空雖然容受萬物,且以撫育萬物為職志,虛空的本身,卻是寂寂寞寞,無色無臭的。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古來聖哲之士,不論出世的抑或入世的,他們皆從寂寞中來,那是毫無疑問的。雖由各人對於寂寞的運用有廣有狹,對於寂寞的體認有深有淺,而致聖格與聖階的範圍等次,各有差別,然其認定寂寞之可貴,乃是一樁事實,即使他們未嘗用過寂寞一詞的字樣。
人類思想的凝聚,必須有其冷靜的機會;人格的昇華,必先假以沉澱的時日。一缸混水,澄清之後,始能明淨如鏡而徹上徹下,但如不讓其有休息的機會,時時均以器物攪之拌之,那是不會澄清下來的。
世間固有不假造作的天才人物,一出世來,即能顯赫一時,但那總是浮淺的,好像肥皂的泡泡一樣,也能吹得很大,也能在陽光之下發出絢麗的色彩,也能使人對之欣然而笑,然其彩色的生命是有限的,其為人們所留下的印象與影響也是有限的。
世上一般的所謂凡夫,總是不甘寂寞的,總是想盡方法,要使自己比他人好,要使自己站在他人的面前與上面,要使自己讓他人看到,要使他人知道自己是比他人為好為高。所以一般的政客,口頭上喊著為民服務,事實上卻在踏著人民的背脊,登上自我高大的寶座,政客之所以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端在他們的不甘寂寞,他們是為成全自我而利用他人;政治家之所以能夠萬民愛戴,留芳千古,原因是在他們的動機為救國家為救人民,能置個人的成敗毀譽乃至生死於度外,他們為了達到自救救人的目的,可以接受天下人的反對,即使在天下人的一致反對之下,他們仍能我行我素。所以歷史上的孔孟諸子,他們各有其政治理想的政治計劃,但他們卻未有一人是能即身而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全部實施的,甚至永遠未能付諸實施的,可是,他們那種獨立特行、獨往獨來而甘於寂寞的精神,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魄力,實在值得吾人深心嚮往。
吾人在寂寞的時候,不能不感到無聊,這是因為沒有寂寞的習慣,未能將寂寞的境遇,看作知己的朋友,所以大家喜歡往熱鬧的場所跑,希望能有一些可以交談的朋友,可以共同玩樂的朋友。但是人從熱鬧的場合中走回家裡時,或當朋友們各自分散時,卻會感到加倍的寂寞,好像自己是生活在古墓之中的木乃伊,孤孤零零,淒淒切切,冷冷清清,像一個無依的幽靈,像一隻失群的小鳥。於是產生反常的心理:越感寂寞之惱人,越向熱鬧的場合裡鑽,越鑽越感寂寞,越感寂寞越要找刺激。最後,心靈混沌了,肉體麻痹了,精神墮落了,整個的人生,也就毀滅了!
當然,凡是尚有一些自制能力的人,那是不會一直走下去的。普通的人,無聊的時候,可以看看書,寫寫字,聽聽音樂,時間也就打發過去了。但是,假如我像魯濱遜一樣,生活在一個無人的荒島上,那裡沒有文明,沒有文化,也沒有任何的書籍,那時候,我是自殺呢?還是繼續活下去?如果我是一個聖者,這倒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環境了,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他要單獨跑到雪山去枯坐六年,耶穌成道之前要到西奈山去獨住四十晝夜,他們何嘗是從書本中找智慧呢?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是中國儒家的主張。書本之中,固可找到知識,真正的智慧,則非書本之中可以找到。所以佛教的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主張直下悟入,明心見性。中國儒家,雖有悟的境界,但在宋明之前,殊少直接點出悟之重要者,到了宋明之後,因受禪宗的影響而標明瞭悟的觀念,陽明的龍場悟道,便是一例。雖然佛教的悟道與儒家的悟道,在層次與成色上有其差別,但其悟的方法是一樣的。如何才能悟道?首要在於知止,以不變而應萬變,心不變動就是定境,心如止水,自可內外明澈,而能自悟悟他了。唯此知止不變的工夫,若非甘於寂寞的人,那是用不上力的。
人之自高自大者,正因他是無知;人之能夠敬上而謙下者,正因他能知道自己之無知;人之無知而能自知為無知者,他已不是等閑的人物了。所以蘇格拉底自謂他之過於人者,只是自知其無知而已!但要發覺自己的無知者,非要有寂寞的經驗不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是不能自知其無知的,一個不能領會寂寞的人(像無有思想可用的動物一樣),更是無法自知其無知的。故如莊子所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警覺心,在一般人來說,那是談不上的。
可是,我們不妨從現在開始,找一個寂寞的機會,或在深夜的床上,或在傍晚的天井裡,或到空曠的原野,或到汪洋的海邊,或坐林間的樹下,或宿深山的梵剎,先讓自己寂寞下來,然後再向自己發問:
我是什麼?我從何處來?又將往何處去?
我認識自己嗎?認識些什麼?認識了多少?
我為何生在天地之間,如何生在天地之間,天地之間如何使我生存?
我對我的週遭事物,理解了多少?理解些什麼?
我是人?人應如何?我已如何?
我覺得人生是痛苦的還是快樂的?痛苦何處來,快樂何處去?自知有苦樂,也能知道他人有苦樂嗎?
我生於天地之間,對天地之間的一切萬有,理解了多少?理解了些什麼?
像這些問題,任便舉出一個,必將無以回答,即使勉強回答,此一答案的分數,必也少得可憐!即使是集古來的大宗教家、大哲學家、大科學家,數千年研究的大成,也只說出了一點一滴、片鱗半爪而已。釋迦世尊,雖稱正遍知覺,但其所覺的形上境界,乃是唯證乃知的,乃是不假言說的,我們凡夫,自也無法從佛教的經論之中找到本末究竟。此一本末究竟或事物終始,仍須吾人從寂寞之中去開悟出來。
偉大的人物,都是從寂寞中來的,也唯有從寂寞中來的人,更能值得人們的尊敬。像西洋的哲學家中,斯賓諾莎甘於磨鏡的寂寞,尼采甘於病痛的寂寞,其餘如霍布士、笛卡兒、洛克、萊布尼茲、休謨、康德、叔本華等,皆甘於獨身的寂寞。中國自顏回以下,賢哲之中,甘於陋巷布衣的寂寞者更多。縱使學優而仕,身居顯要,但他們總是耿介質直,不阿不求,從政是為兼善天下而已,正是學以致用的表現。唯於偉人之中,寂寞一生者之精神作用,遠較及身聞達之流,更能使人崇敬與嚮往,卻是一個事實。這在宗教的行誼之中,尤其明顯,一個高僧,只要能有徹底放下的決心,他們對於寂寞的生活,必能甘之如飴,世人視之為枯槁,他們住之如春風。因為一個真正的宗教家,特別是一個佛教的僧人,他們雖以出世為宗旨,卻以入世為手段,他們的徹底放下,為的是要絕對的承當,若不先做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工夫在前,自也無法擔起自救救人救眾生的重任在後。即使一個高僧,未嘗真的在其一生之中,度盡一切眾生,但卻願於生生世世,盡未來際,直到度盡眾生為止,正因有其弘願之所在,他們雖然枯坐於水邊林下,亦同於心包太虛而與一切眾生談天說地了。近代的佛教界中,有一位弘一大師,他於出家之後,總是隱藏,總是甘於過他寂寞的生活,他在生前,著作無多,化眾甚少,但其若有所言,必是悲憫懇切之詞,必能語語感人,故到目前為止,不論僧俗,凡是知之者,談起弘一大師,總會肅然起敬,這就是受他那種卓拔的人格所感。那種卓拔的人格,卻是從寂寞的生活中,貞凝而成的。
一個甘於寂寞的人,根本不會想到寂寞的問題。人在單獨的時候,會覺得寂寞,有了一個朋友交談,便不寂寞了;一個甘心與寂寞為友的人,卻將一切寂寞中的人當作自己的朋友,他將全部的心力,放在寂寞的朋友身上,為之發掘問題,並為想出解除問題的方法,以期拯救,以期安頓。因為凡人皆在寂寞之中而又不忍甘於寂寞,不甘寂寞的人是愚癡的,也是痛苦的,所以凡人皆在他的拯救之列,凡人皆是他所關心的朋友。那麼試問:能以一切人乃至一切眾生為朋友的人,他會感到寂寞嗎?當然是不會的。
若想甘於寂寞,確非輕易之舉,如果以甘於寂寞作為來日的晉陞之資,期以十年寒窗,換取來日的衣錦榮貴,那是流俗的,那不叫作甘於寂寞,而是做的投資生意。離俗而處者,固為甘於寂寞的人,一個真能甘於寂寞的人,卻並不一定要離群獨居,像美國的林肯,像印度的甘地,都是寂寞的人。寂寞者不會考慮到自己的問題,他只希望同情一切人,了解一切人,並願為一切人乃至一切眾生承擔問題而解除問題,他是忘我的,即使一切人乃至一切眾生都把他當作敵人來攻擊,他也必能在所不計,人皆以他為敵人,他卻仍以朋友乃至慈母的心懷來愛之護之。所以佛教主張學佛者,應先空去一個我的觀念,然後才能進入佛法的聖階,因為人欲皆由我的觀念而來,有我就有人欲,有人欲便不能甘於寂寞。
寂寞是可貴的,願將此一短文,獻給正在寂寞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