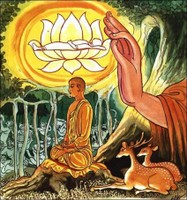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
我的出身,家父是單傳,據說他出生二十八天,我的祖父就去世了。在他十餘歲的時候,我的寡祖母也去世,只剩他孤苦零丁一個人。我出家的生活就和他的單傳一樣,出家人都有同門、同宗,濟濟多士,但我的師父和我的師兄都早逝,尤其我人又來到台灣,更加的孤單一人。
感謝因緣際會,開創佛光山之後,出家的弟子就有一千三百人,還有入道的教士、師姑百人。台灣的寺廟都很小,一時之間,有了這麼一個像叢林的大寺,就經常有人來追問我怎樣管理?貧僧沒有學過管理,也不懂得管理,只覺得大家志同道合,為佛教、為社會大眾奉獻服務,重視因果,在公開、公正、公平、公有之下,就會相安無事了。
有一位出家的徒眾是香港大學管理學系畢業,在四、五十年前,管理學科就已經有人注意。所謂人事管理、財務管理、學校管理、圖書管理、醫院管理、工廠管理等等,貧僧看到這位徒眾自恃高學歷畢業,心有所傲,就告訴他,管錢,錢不講話,隨你用法;管物,物也不開口,隨你搬動;管人,就難了;但管人也還不太難,最難的,是要管自己的「心」啊!你會管「心」嗎?
貧僧童年失學,不但沒有進過學校念書,連學校都沒有看過,曾經有一次台灣大學邀我去講「管理學」,當然我不敢應允。雖然佛教也有管理學,像叢林兩序大眾、四十八單職事、清規戒律等,這些我都沒有做過深入研究,哪敢對人講管理呢?
後來,曾經擔任過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先生,他在陽明山創辦了中國文化大學,並且在民國六十九年(1980)找我去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他致詞時說:「整個華崗就是一個大叢林,在此歡迎我們的住持星雲大和尚回來。」我聽了以後心有所愧,雖然在佛光山開山,但也不敢自認是住持。因為一個住持,要對叢林四十八單職事、清規戒律相當熟稔,所謂住持三寶,我想貧僧還不夠條件。
前幾年,台灣大學副校長湯明哲教授要來對我做一次訪問,我和他並無交往,但貧僧對別人的要求一向不願意拒絕。他來了就問:我對你們感到很奇怪,我們在家人有週休二日,有年節放假,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增加休假的時日;我們在家人每個月有數萬元的收入,但仍然感到不夠,希望再增加一些薪水。聽說你們有一千多名出家人,沒有假日,沒有薪水,晚上還要加班,挑燈夜戰,有這種力量是什麼原因呢?
像這樣的問題,過去不曾有人問過我。聽他這麼一問,忽然感覺它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回答說,你們在家人是過「有」的生活,有假期、有待遇、有財物、有家庭,有妻子兒女,有,是有窮有盡、有限有量,當然會嫌不夠;我們出家人過的是「空無」的生活,無假日、無薪水,心甘情願為社會大眾服務,沒有指望報酬,因為沒有這個慾望。因為「無」,所以無限無量、無窮無盡。他是台灣大學的名教授,對我這樣的回答,我不知道他內心的反應是如何了。
說起佛光山的管理學,貧僧覺得,只要肯得上下大眾同甘共苦,只要心平,又何處不能自在呢?當然,我也經常告訴僧信弟子「不比較、不計較」,不把人我是非得失放在心上,日子就會很平安的度過。我寫過一首〈十修歌〉,就是希望對修道者有所勉勵,後來漸漸的也為大家所傳唱。
「一修人我不計較;二修彼此不比較;
三修處事有禮貌;四修見人要微笑;
五修吃虧不要緊;六修待人要厚道;
七修心內無煩惱;八修口中多說好;
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
若是人人能十修,佛國淨土樂逍遙。」
我也主張要有「老二哲學」的思想,所謂「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我們觀看歷史,歷朝的第一代皇太子被害的為數居多,如隋朝的太子楊勇,如唐朝的李建成等,多為了出頭遭忌而犧牲。如果每個人安於「老二」,懂得「無我」,對做人處事,也就會心安理得了。
我也覺得佛門裡教我們的發心、忍耐,是非常有用的。發心就有力量,發心就會心甘情願,發心為佛教服務、發心要廣度眾生、發心為常住工作、發心肯吃虧耐勞……能發心,還有什麼得失計較的呢?
忍耐,更是重要。不但做一個出家人,世間上每一個人要想生存、生活,都要能忍。能忍,就知道人我的關係,就知道情緒安定的重要。人家一句話、一件事,跟我來往,都要我去認識、接受、負責、擔當、處理和化解,都要有忍的智慧、忍的力量。
因此,貧僧很早就寫了一首〈剃度法語〉,告訴要求入門的弟子,假如你要問我怎樣做一個出家人?對出家人的看法是什麼?這首〈剃度法語〉就不光只是唱一下而已,你必須好好思量。這是身為佛光弟子必須實踐、奉為圭臬的座右銘:
佛光山上喜氣洋,開山以來應萬方。
好因好緣多好事,青年入佛教爭光。
發心出家最吉祥,割愛辭親離故鄉。
天龍八部齊誇讚,求證慧命萬古長。
落髮僧裝貌堂堂,忍辱持戒不可忘。
時時記住弘佛法,莫叫初心意榜徨。
為僧之道要正常,不鬧情緒不頹唐。
勤勞作務為常住,恭敬謙和出妙香。
清茶淡飯要自強,粗布衣單有何妨。
生活不必求享受,超然物外見真章。
善惡因果記心房,人我是非要能忘。
深研義理明罪福,慈悲喜捨道自昌。
朝暮課誦莫廢荒,念經拜佛禮法王。
無錢無緣由他去,只求佛法作慈航。
十年之內莫遊方,安住身心細思量。
任他天下叢林好,我居一處樂無疆。
在些法語裡,貧僧沒有更改過去傳統出家精神的意涵,一個出家人本來就要依止一個常住,好好安心辦道。
在佛光山,因應社會結構的改變,是到最近十年,才改為五點半早覺。在此之前,全山大眾早晨四點半起床,五點禮佛做早課,六點鐘過堂,七點鐘在教室聽講學。三個小時後,聽板聲十一點半過堂用齋,飯後跑香,稍微休息一個小時,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繼續上課。然後出坡服務一小時,四點半盥洗、用藥石(晚餐)。晚上七點自修複習,九點鐘晚課拜願,晚上十點,在鐘鼓聲之下養靜睡眠。星期六、星期天,人來客去,除了上課以外,還要分班去接待客人參觀、服務三餐,為大家典座行堂分食。
有時候,外請的老師只有在禮拜六、禮拜天才有時間前來授課。經常在教室裡,老師一來就是一整天的課程,甚至把晚上自修的時間,都用來講學。解門之外,行門修持有:抄經、打坐、朝山,二六時中,佛聲不斷。
雖然外面也有人批評我們,但貧僧常有一個感覺,想問批評我們的人:你們能每天在教室裡面坐六到八個小時上課嗎?你們能每天三餐過堂,陳年累月的一飯一菜嗎?飯前飯後念〈供養咒〉、〈結齋偈〉,至少要花一小時吃一頓飯,你們能做到嗎?你們能可以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晚上十點鐘休息嗎?你們能每日早晚功課、隨著鐘鼓板聲作息嗎?你們能為常住出坡辛勞,不會埋怨嗎?但佛光山所有的貧僧們,每天為佛教、為大眾服務,盡管如此忙碌,忙得很開心,忙得很有意義,每個人幾乎都笑逐顏開,天天好似過年。
如果我做貧僧的話,佛光山所有的徒眾一千餘人,他們也應該都叫貧僧。其實,你問他們有錢沒有錢,可能他說沒有,但你問他生活得歡喜不歡喜,他必然會告訴你生活得非常歡喜安然,不然,為什麼要出家做「貧僧」呢?
不僅如此,為了樹立佛光山的宗風思想,維護山門綱常紀律,貧僧也為徒眾立下「佛光山十二條門規」,作為四眾弟子依此修道的準則。這十二條門規是:
一、不違期剃染; 二、不私建道場;
三、不夜宿俗家; 四、不私交信者;
五、不共財往來; 六、不私自募緣;
七、不染污僧倫; 八、不私自請託;
九、不私收徒眾; 十、不私置產業;
十一、不私蓄金錢;十二、不私造飲食。
在佛教裡,這些規矩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容易。因為,佛光山不是個人,而是一個教團,佛光人的作為,不能只為個人求安樂。凡有所作,都要想到團體、大眾,都要顧及團隊精神,要有「大我」的觀念。大眾依共同法則、共同制度,共同所信、共同所依,共同的自由,做為行事的準則,這就是所謂「集體創作、制度領導」。
後來,跟隨貧僧的徒眾、信徒漸漸增多,想到台灣大學的師生都自稱「台大人」、文化大學的華岡師生也稱「華岡人」,因此,凡與佛光山有緣的人,都應可以稱為「佛光人」。為了建立大家的共識,於是貧僧又陸續立了〈怎樣做個佛光人〉十八講,讓僧信大眾對於佛光山的宗旨、目標、道風、守則,有一個深切的認識。十八講的內容,可以參閱《人間佛教系列。佛光與教團》。
我也告訴徒眾,凡事要抱持著「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信徒」的精神行事。
所謂「光榮歸於佛陀」,指的是雖然佛光山大眾人多共事,但是個人不可爭功、不可執著,要隨喜隨眾,一切的光榮都是集體創作、仗佛光明而有。
「成就歸於大眾」指的是,佛光山創辦的佛教事業,都不是我們個人能力所及,一切都是全體大眾共成的。
所謂「利益歸於常住」,在佛光山,一切都依佛陀建立「六和僧團」的理念而行事。「六和」是指戒和同遵(法制的平等)、利和同均(經濟的均衡)、見和同解(信仰的一致)、身和同住(和樂的相處)、口和無諍(語言的親切)、意和同悅(心意的開展)。在佛光山常住裡,雖然個人不富有,但也沒有人為生活憂心,無論衣、食、住、行、生病、旅行參學等,一切都有常住照顧,因為不私蓄、不佔有,可以說是無憂無慮的佛國淨土了。
而「功德歸於信徒」,則是說信徒在這發心、修行、奉獻、護持,一切的緣分、功德都應該有他們一份。
以上種種說來,其實說我是「貧僧」,除了金錢,這許多的思想、理念、制度,甚至三好、四給、五和、六度……都是我的財富法寶。若要問貧僧的管理學是什麼?實在說,貧僧的管理學就是在大雄寶殿的規矩裡,在禪淨法堂的法制裡,在典座齋堂的發心裡,在勞動出坡的作務裡,在人我關係的和諧裡,在佛法正信的悟道裡。我希望佛光山適當的貧窮,過清貧的生活,這就是中道的管理學。除此之外,貧僧還有什麼管理學呢?所謂「有佛法就有辦法」,有了佛法,又怎會去怨天尤人、慨嘆自己呢?
原來世間上不是以有錢、無錢來論貧窮富有,貧、富,還是在心裡上的感受。行文至此,對於自古以來在大陸叢林流行的「貧僧」兩個字,貧而不貧,自然也就理所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