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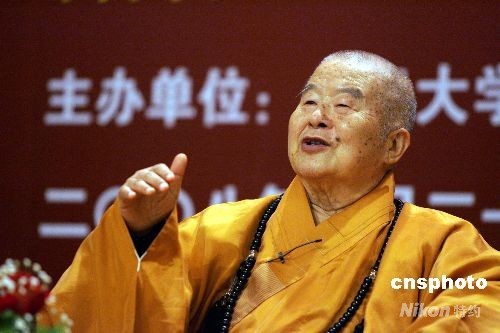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我從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下來,將寺務交給心平處理。在傳法大典那天,記者們目睹滿山滿谷的人們對我種種恭敬,甚至匍匐迎送,好奇地問我何以致此?我突然想起國片「我就這樣過了一生」這句話,心中不禁感觸良多,回想大家對我的肯定,是自己付出多少的辛苦、忍耐所換取來的成果啊!如果將這部片名換一個字,改為「我就這樣忍了一生」,用來形容自己,應該是很貼切的寫照了。
我從小生長在亂世裡,先是軍閥割據,外強環伺;繼之中日抗戰,後來國共對立,家鄉的經濟本來就很落後,加上這些人為的禍患,生計更是困難重重。在糧食極為短缺的當時,我吃過麥渣糊粥,我以地瓜當飯,每天三頓,吃得都怕了起來。十二歲出家以後,寺裡仍是以稀粥代替乾飯,經常一個月吃不到一塊豆腐,或一些素菜。這對於正值成長期間的我來說,當然是不夠納胃的,但是想到時代的艱辛、常住的難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卻了飢餓之苦,就這樣我養成能忍的習慣。
一九四九年,剛來到台灣時,我四處飄泊,無人收容,真正遇到難以度日的苦楚。不過,忍是一種力量,我開始與生活搏鬥,與命運挑戰。後來我輾轉來到宜蘭,生活才逐漸安定下來,當時正信佛教不發達,為了接引更多的人學習佛法,我不惜將些微稿費、嚫錢拿來購買佛教書籍,送給來寺的青年;我甚至經常忍饑耐餓,徒步行走一兩個鐘點以上的路程,到各處講經說法,將飯錢、車費節省下來,添置佈教所需的用具。佛教第一次傳教用幻燈機、錄音機、擴音器,就是那時購買的。
隨著弘化區域的逐漸拓展,聞法信徒的日益增多,我發現到人生的問題無窮無盡,心中益發體會佛陀示教利喜的悲心宏願,因而更加激勵自己以弘法利生為己志,所以凡有人前來請法,無論路途遠近,我都欣然答應;凡信徒有所請求,不管事情難易,我也盡量化解其憂。
說到弘法,光是交通,我那時騎過單車、坐過牛車、煤礦坑道用的輕便車、三輪車、手拉車,當然火車、汽油車,甚至騎馬、乘轎、飛機、小船統統在內。
爾後數十年來,我常常因為接引信徒,從早上講到晚上,我時時由於行程緊湊,耽誤了用餐的時間。有時為了方便起見,我乾脆以冰水泡熱飯,或以熱茶泡冷飯,聊以充飢;有時剛要舉箸用餐,卻臨時接到邀約,我只得端起碗來,管它裡面裝的是滾湯,還是熱面,唏哩呼嚕地,一併倒入嘴裡,也顧不得燙破舌頭,更遑論是否填飽腸胃了。所以盡管這些年來稍有餘裕,我還是經常食不飽腹,就這樣,我可以說是忍饑耐餓過了一生。
早年因為沒得東西吃,只要有得吃,都覺得好吃。近年來,吃的東西很多,我十分珍惜這份福報,所以不管是湯面、拌面,乾飯、稀飯,米粉、冬粉,水餃、包子,雖然不一定覺得好吃,我一概來者不拒。偶爾放在一旁不吃,是因為忙於赴約,或者當時已用過,並不一定表示心裡不喜歡。有時候看到徒眾很用心地為我準備了一道菜,為了嘉勉他們的辛勞,即使不甚好吃,我也會隨意稱讚某一道菜十分可口。然而徒眾未能善體我心,甚且誤解人意,有時候一月半月每天都會吃到同一道菜,問他們是何原因,他們總說是隨順我的喜歡,令我真是啼笑皆非,但是叫我說一句不喜歡吃,怎樣我也不肯,我寧願一直忍下去,也不願隨便說出我的好惡。
最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大家「傳說」我喜歡吃素烏魚子。過去曾經有一段時期,每一餐飯都有一盤素烏魚子擺在我的面前,其實我因為嫌其味道太重,從來不曾動過一筷,吃過一口,所有上桌的素烏魚子全都是被其它人挾了去,只是大家不察,以訛傳訛,甚至還有人誤以為真,特地買來送我。對於大家的這番「錯愛」,我也只有一直忍了下去。
類似這種事情,還真是無獨有偶呢!例如:多年以前,信徒送了我一塊佳美香皂,當時物質十分短缺,舶來品更是稀有難得,大家看了十分羨慕,但是我仍舊慣用一般的肥皂,所以一直將它擺在洗手台上,未曾動用。奇怪的是那塊香皂的體積居然日漸減少,後來大家都說我喜歡用進口的佳美香皂,我聽了也只是忍笑而不語,心想能夠讓大家的喜好成為我的喜好,不也十分有趣嗎?有一回在外地講經,天氣突然變冷,有位弟子為我買了一件毛衣,我連說:「厚的衣服真好!」意在讚美他的用心體貼,沒想到日後大家都說我喜歡穿厚的衣服,從此盡管天氣轉熱,侍者也依舊為我準備厚的衛生衣、厚的羅漢褂,乃至特地訂製厚的長衫大袍,我向來不忍拂逆別人的好意,因此只有自己忍受汗流浹背之苦了。
我常常想起過去在叢林裡,戒規十分森嚴,即使是天寒地凍,也不准我們披圍巾,戴帽子,而在那個貧苦的年代裡,我們身上穿的幾乎都是已圓寂的前人遺物,縫了又補,補了又縫的單衣薄衫,每逢隆冬時節,凜冽的北風從寬大的衣領袍袖中直貫而下,沒有忍耐精神,不易度過寒冬。所以我後來到了台灣,只憑一件短褂,度過北部兩個冬天。這時,目睹一些出家人,才有一點寒意,就全副御寒配備加身,一眼望去,似乎少了幾分道氣,在慨嘆之餘,不禁感謝以往師長的嚴格教育,培養我無比堅忍的耐力。於今,我將這份耐冷的力量運用在忍受暑熱上面,顯得駕輕就熟,但是弟子們是否能感受到我這份包容的心意呢?
所謂「忍」,忍寒忍熱,這是很容易的,甚至忍饑忍渴,也算不難,忍苦忍惱,還能勉力通過,然而忍受冤屈,忍一口氣,就大為不易。但是,無論如何,想到自己既已學佛,深知相互緣起的真理,明白「忍」是一生的修行,為什麼不能依教奉行呢?
曾經有一位徒孫,經常購買下端繡有圖案的毛巾給我使用,我因為臉上破皮,建議他買沒有花樣的,以免洗臉時覺得不舒服,他卻理直氣壯地說道:「有圖案的毛巾比較美觀,您用另外一端擦臉,就不會碰到繡花了!」唉!彼此心境不同,說起話來有如對牛彈琴,我也只有當下「受教」,忍他一忍算了。
有時侍者為我準備飯菜,不是少拿箸匙,就是奉上一雙長短不一的筷子,我既不起身自取,也不予以責怪,待別人發現告訴他時,只見他毫無愧色,哈哈大笑就掩飾過去了。
記得我五十歲生日那年,一名在家信徒特地送我一張價值不菲的彈簧床,無奈我從小睡慣了木板床,但又不忍直言,讓他難過,從此只好將床當做裝飾品,自己每天睡在地板上,達十年之久。
有一次,我應邀到溫哥華弘法,承蒙信徒好意,特意為我商借一位張姓居士的別墅,其中一套考究的浴室,內有新式開關、長毛地毯,還有美輪美奐的浴簾、浴池,我因為不會使用這些繁複的裝備,只得忍耐到行程結束,回到佛光山再痛快地洗。
又記得韓國的頂宇法師、多倫多的土地經紀人溫居士,為了表達對我的尊敬,他們訂了五星級的總統套房給我住。然而我看到內部裝潢之富麗堂皇,捨不得使用,只好整夜不倒單坐在沙發椅上,直到天亮。
朝好的方面去想,這也是他們的一番孝心善意,我怎好苛責呢?尤其回憶四十年前,我剛到宜蘭雷音寺時的光景,與今比之,真可說是天壤之別。
那時由於政策使然,寺院裡住滿了軍眷,丹墀成了大眾的廚房,每次如廁,我都必須等人將煮飯的爐子移開,才能開門進去。最初我都在佛桌下過夜,後來寺眾整理出一間斗室給我居住,裡面除了一張破舊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舊的縫紉機,但是我已經很滿足了。每次睡覺的時候,我總是小心翼翼,一躺下來,就不敢翻身,唯恐竹床咿呀作響,吵到別人。
三個月以後,我從佈教的監獄撿來一把獄所不用的椅子,欣喜不已,從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寢以後,我就把佛前的電燈拉到房門口,趴在縫紉機上寫作。在現代人看來,或許感到不可思議,但是當時的我,非常珍惜這份難得的機會。那年,我二十六歲,平生第一次使用電燈,以前在棲霞山、焦山、宜興、中壢、青草湖等地,都沒有電燈,所以,盡管群蚊亂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有時寫到次日破曉,耳聞板聲,方才休筆。
三四十年後的今天,目睹現代的年輕人空腹高心,漫言入山修行、閉關閱藏,不禁感慨萬分,倘若福德因緣不具,焉能獲得龍天護持?「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沒有百忍興教的精神,如何成就人生大事?「我就這樣忍了一生」,豈止是就物質上的缺乏而言,其它如精神上、人情上、事理上、尊嚴上等種種違逆境界,又何止忍上百千萬次?一九九一年,我在浴室裡跌斷腿,頓時身邊增加不少「管理人」,這個徒弟要求我不能吃這種食物,那個徒弟告訴我不能用那種枴杖,過分周到的看護,使我備感束縛。有時因為身體不適,這個弟子拿來這種藥,那個弟子拿來那種藥,我為了圓滿大家的好意,只得忍耐把兩種藥都吃下去。有些信徒說美國好,叫我去美國度眾;有些信徒說澳洲好、非洲好、歐洲好,也希望我前往弘法。我為了滿足大家的「好」,所以,只有忍耐旅途勞頓,到處飛行雲遊。
雖然百般無奈,但是想到為師者在他們的心目中永遠年輕,也只有自我解嘲了。有時回頭反省:「為人著想」固然便利了別人,卻也讓我「就這樣忍了一生」。我的腿子之所以會摔斷,正是因為在盥洗時聽到電話鈴聲,為了怕對方著急,趕緊從浴室衝出來時,不慎滑倒所致。雖然有了這次前車之鑒,我還是盡量不讓電話鈴聲超過三聲以上,與生俱來的性格實在不容易改掉啊!
回顧我這一生自從擁有電話以來,真可說是不堪其擾。我常常在深更半夜被西半球、南半球打來的電話吵醒,拿起話筒一聽,往往都是些不痛不癢的小事,盡管心中也在責怪他們不知體諒別人,預先算好時差,但是仍然出語和緩,不使對方難堪,而我自己卻賠上一夜的失眠。
事後被一些徒眾知道,總是勸我:「師父!您不要管他們,晚上睡覺前,將電話線拔掉。」但是我從來未曾如此做過,天生不喜歡讓人失望的性格,使我注定「就這樣忍了一生」。
我不但在半夜耳根不得清淨,即便在白天,也還得六根互用,手腳並行。在我的法堂裡,總是聚集著一群徒眾,七嘴八舌地和我討論事情,我不但得瞻前顧後,還必須左右逢源,唯恐忽略了那一個人。有時大家為了公事僵持不下,我還得居中斡旋調處,幾個小時下來,真是口乾舌燥,精疲力盡。
出了法堂,還有人要我路上辦公,拿著一疊表格報告,希望我能指點一二,我雖然按捺性子,有心成就,偏偏這時往往半路殺出程咬金——遇上了信徒遊客,又是對我合掌禮拜,又是要求合影留念,明明短短五分鐘的路程,也得走上半個小時。
從十年前多次帶團出國訪問,到近年來頻至世界各地弘法,更無所謂樂趣可言。常常飛行數小時,一下飛機,就被人簇擁而行,照相、講話佔了大半時間,連洗把臉、上廁所的空隙都沒有,不到深夜,無法回到寮房裡小憩。每日如是,週而復始,十天半個月後,再坐車到機場,飛到另一個地方。雖說行腳各地名都大邑,實則不曾盡興觀賞;雖說走遍世界名山大川,實則未嘗仔細探訪勝地,只是到而不到,聊以告知來此一遊罷了。
數十年來,佛光山大小道場幾乎都是在我的手中建立起來,完成以後,即刻交給弟子們管理,裡面的一桌一椅、一磚一瓦,都含藏我多年來的經驗與理念。但是弟子上任以後,既未能善體我意,又不前來請示緣由,就輕易地改隔間,挖牆壁,甚至換佛像,更制度,當我再度前往巡視時,一切已經「面目全非」,擔任住持的弟子還在一旁問我:「改得好不好?」我一向不喜歡否定別人的主張,即使心中不以為然,也只有說「好」。雖是多少忍耐點滴在心頭,但我這一聲「好」,休卻了多少麻煩,給予人多少歡喜,泯除了多少代溝的問題,說來還是頗為值得的。
我有出家弟子千餘人、在家信徒百餘萬,但是他們高興時不會想到來找我,一旦上門,必定是有了煩惱,而且大多聲稱是來掛「急診」的,我再忙再累,也只得「恆順眾生」,予以接見、傾聽、安慰、鼓勵。憑著自己多年的歷練,倒也解決了不少疑難雜症。但也有弟子對我說:「師父!你只叫我們忍耐,難道除了忍耐,就沒有其餘的辦法了嗎?」確實,我一生惟一的辦法、惟一的力量,就是忍耐。
回顧我的一生,正如同陳誠所言:「為做事,必須忍耐;為求全,必須委屈。」雖然「我就這樣忍了一生」,但是喚醒了多少迷惘眾生,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所以,我祈願生生世世再來娑婆,以比丘身永遠堪忍地利濟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