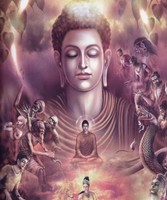佛弟子文庫
佛弟子文庫
司馬光生性不喜華靡,素以儉朴自守。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住在城郊西北一個小巷中,居所極為簡陋,僅能擋風遮雨。夏天為避暑熱,他請工匠挖地丈餘,用磚砌成地下室,讀書寫作其間。大臣王拱辰當時亦居洛陽,所建宅第凌天高聳,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鑽天,司馬入地。」邵康節則打趣說:「一人巢居,一人穴處!
司馬光不收任何人送給他的禮,就連皇上的賞賜也不受。仁宗皇帝臨終前立下遺詔,賜予司馬光等大臣一筆價值百餘萬的金珠。司馬光考慮到國家財力不逮,便領銜上書請免。力辭再三未果,只好將自己那份珠寶交諫院充作公費,金錢接濟了親友,自家分文未留。司馬光為官40年,僅有薄田三頃,所得薪俸大多周濟了窮人。其妻去世時,竟拿不出錢來辦喪事,只得典當薄田置棺埋葬。司馬光臨終床簀蕭然,唯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呂公著為輓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為黃金。」
司馬光府上有個僕人,30年來一直稱呼他「秀才」。前來拜會的蘇軾,聽後覺得不恭,就教他以後改稱「大參相公」。作為稱呼,「相公」是指「位居宰相之職並享有公爵爵位的人」。司馬光聽僕人突然改口,吃驚地問他誰教的,僕人如實稟告。司馬光說:「好好一個僕人,被蘇東坡教壞了。」在司馬光看來,「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他不僅自己不吝身份,也不希望家人為世俗所染,變得勢利起來。
俗話說,「宰相家人七品官」。在封建社會裡,因勢焰熏灼使然,官宦府邸中人,即便車伕、門子,身價也非同一般。如果家規不嚴、門風不正,他們就會倚權仗勢,尋釁滋事,有恃無恐,橫行不法,甚至貪污受賄,作奸犯科。據《清仁宗睿皇帝實錄》記載,和珅的大管家劉全,查抄資產竟至20餘萬,並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即便在今天,領導「身邊人」犯罪的案件也時有耳聞,這在司馬光家人身上是不會發生的。
一天,司馬光經過獨樂園,見新蓋了一間廁屋,就問守園者,建房的錢是從哪裡得來的。守園者答,是我把遊人給的賞錢積攢起來的。司馬光說,為什麼不留著自己用?守園者說,難道只有相公您不要錢?守園者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句反問,就把主僕雙方的為人都說清楚了。賞錢屬於個人正當得利,留為己用合情合理,守園者卻用於公共設施,這顯然超越了一般職業操守。也許是我們對那些假公濟私、中飽私囊的行徑看得太多了,愈發覺得這位守園者可敬。他能這樣做,無疑是受到司馬光的熏陶。人格的魅力有多大,影響力就有多大。
在司馬光手下當差,無勢可仗,無光可沾,也無油水可撈,顯然要比其他公府豪門清苦。但因主人夫婦待之以誠,持之以禮,從不欺凌打罵,他們活得自在有尊嚴,心裡感到踏實,這可不是金錢能夠買得來的。他們不僅安貧若素,沒有怨言,而且也像主人一樣平和敦厚,不慕奢華,不圖富貴,老老實實做人,勤勤懇懇做事。
行勝於言,溫公家風的形成,很大程度源自身教。「修齊治平」四字,司馬光踐履得十分到位。他深知「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儉能立名成業,侈必墮落自敗」,並視為「大賢之深謀遠慮」。因此在身教同時,非常重視言教。《訓儉示康》一文,就是司馬光專門教誨繼子司馬康的。
由於身教言教並重,其家族後人也都以賢德立身,絕無「官二代」之累。司馬光一生著述頗豐,收入《四庫全書》的就有16種457卷。影響力大的除《資治通鑒》外,就是《家范》了。《家范》廣泛收集了治家有方的實例,係統闡述了家庭倫理關係、治家原則以及修身處世之道,為歷代推崇的家教範本。司馬光自己說,《家范》比《資治通鑒》更重要,因為家風是世風之基。